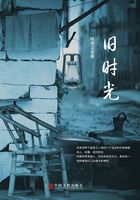
大戏曲小走笔
引子
中华戏曲,历史悠久,剧目繁多。光优美唱腔、经典唱词就汪洋恣肆。大致统计,仅剧种就有三百余。
最早的戏曲大约出自唐朝盛期,且与皇室有关系。古籍记,唐明皇在工作之余,常与杨贵妃到皇家林苑的梨树园,同一帮伶官击鼓做戏。故戏曲界叫“梨园行”,祭的祖师就是李隆基,演员则自称为梨园子弟。
随后,梨园戏传至民间,兴旺表现应是在宋、元盛建的“瓦舍勾栏”。“瓦舍”相当商业游艺场,类似大集市或商业活动中心;“勾栏”则为设在游艺场的“俳优篷”,即演出场地。每座“瓦舍”都建有多个“勾栏”,足见昔年戏曲鼎盛如日中天。
现存最早的剧本为南宋的《张协状元》,距今约800年。写蜀生张协,赴京赶考,途遭强盗,病倒破庙。幸得村姑搭救,殷勤照料;心生爱慕,喜结秦晋之好。村姑卖发筹川资,助张协赴京中状元。久之,村姑京城寻夫,竟被张协从官邸打出。遇丞相相救,认作义女,曲折经历,方使夫妻团聚。
故事不新鲜,类似《金玉奴》和《铡美案》,可算当今负心汉的古代戏曲版。
但是,我对戏曲的喜欢,并非先对其知识有所了然,而是从小的耳濡目染。
一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五、六岁,所居川北古镇,颇适宜戏曲生存。古镇依山傍水三面环江,鸟瞰尽是鳞次栉比的明清瓦房。古城墙苍苔布满,老街面石板平展。遇雨天,雨滴屋檐叮咚作响,雨打芭蕉珠绿成趣。整个古镇沐浴在空蒙的雨里,清幽静寂,散发出隔离尘世的气息。
古镇虽三面被嘉陵江环绕,却没一座桥。北门关山巍峨,南门水流湍急,西门礁石嶙峋,倘想进古镇,必须去东门渡口坐乌篷船。船不大,可渡十余人。船篷由竹篾夹竹叶编成,拱圆状,罩船舱,挡雨遮阳。舵舱比船舱高一阶,两舱间的顶棚空一片,利艄公摇橹、掌舵、望对岸。木桨两把,左右各一。船头立一人,撑篙、拔锚、收船票。待过河者坐好,便吆喝一嗓道:“开船了——”。艄公这才点燃叶子烟,神情悠闲,桨击水面,漾起水圈,水圈宛如青绿光环。
夕阳沉西,凉风渐起,轻点长篙,船儿徐移。那沿江的打鱼船,如柳叶般,点缀江面。暮霭如烟,渔火阑珊,辉映夜空的湛蓝。耳边隐闻渔歌,时有时断,听不了然。船儿轻扬,两岸花香,飘来川剧《秋江》渔翁那闲适的歌唱:“秋江河一只舟,老汉我打鱼度春秋。打来鲜鱼沽美酒,一无烦恼二无忧……”。
河水汩汩,洒满月光;笙箫泛起,孤鹜飞翔;蓝波粼粼,起伏荡漾——分明是一江戏曲在流淌。
古镇不通汽车,相对闭塞,加之民风较淳朴,当年有段时间,那里宛然是个被社会遗忘的“世外桃源”。
古镇古老,巴蜀文化厚实,使得居民极喜川戏。倘闻剧团来演,老早便巷议街谈,成龙门阵之热点。我等细娃则涌至河边,争看上游飘来的演员船。其间,搬运工最得意,因搬戏箱,可先进船舱,离演员最近,看得最真,让我羡慕得要命。演员气宇非凡,风度翩翩,矫首昂视,爬梯上坎,一直信步进进大西街的老戏园。娃儿妹仔则一路跟着看,乐得屁颠屁颠。
然,那老戏园陈旧不说,纳人亦不多,除却仿古舞台,无一板凳可坐。就这简陋条件,看戏那天,大人细娃还欢喜得像过年。老早即去戏园窗口买票。窗口不高,但细娃太小,又想把看戏“不差钱”的自豪使外人知晓,故排队的娃们真不少。欠高咋办?踮脚尖;再不行,叫俩仨细娃托举,戏票终于到手里。
傍晚,戏园一带,灯火映天,热闹非凡,拥挤不堪。人们扛着长凳短椅,从四条青石板街向西门中心聚集。妇女抱小的,牵大的,那半大不大的,则骑上父亲脖颈,幸福得不行。街两边店铺皆开门,小馆子生意火爆,热流滚滚。椒盐锅盔、牛肉笼笼、海带肉丝面、芝麻赖汤圆……,难以数遍。跑堂的托着摆满佳肴的木盘,拉长声音喊,穿梭食客间;饭菜浓香涌出铺面,顿觉肚儿咕咕叫唤,清口水直咽。
戏园大门已水泄不通,此时最易趁机朝里拱——家境困难,观戏缺钱又想看。然混票有风险,抓住罚你站街沿;父母晓得,定打得你“惊叫唤”。成本太高,实施划不着。我“屡试不爽”的办法是:先在门口听,待散场时分,把门的会提前放人,便可大摇大摆进。而里面早挤得如“贴相片”,离戏台远的只能站上板凳伸长脖颈偏着脑壳看。我则从大人脚底钻,钻到台前吊住台沿探出头脸。看得的确清楚,眉毛胡子都可数。可你刚入戏,唢喇吹腔起,大戏即结局。演员谢幕,大幕紧闭。人流又涌你出去,心里歉歉的。
较为过瘾的是看演出前的排练。小孩不起眼,悄悄溜进园,侧立一边看。不化妆,能看清演员的素颜,倒更觉亲切自然。那咿咿呀呀的练嗓,尤让我心痒;穿着朝靴走台步,拌上川剧锣鼓,艳羡得心都快跳出。你正入迷,必遇管事的,不怕麻烦来招呼你:“哪家细娃?啷个进来的?出去出去。”你低头出去,心不安逸:“格老子的,看下咋啦嘛?会少你个‘指耳朵’呀?”
而2013年底,梅花奖剧团来攀枝花演戏,演出前需走台练习。我得知消息,又混将进去,却没人撵你。不但无人撵,倘想与“梅花”照相,你态度真诚些,大多能如意。两相对比,令人唏嘘。
二
仅我所知,中心古镇就出过好些川剧名伶。与鄙人“沾亲”的,有我儿时寄养其家的七婆婆的女儿我叫“嬢嬢”的冯诗文;儿时好伙伴李次仁之令尊我称“舅舅”的李依仁;以及我的家门“嬢嬢”陈淑华。都是我所崇拜之人,我却很难见着他们。即便相见,亦没搭言——人家乃明星,忙得不行,谁跟你个细娃扯闲筋?略记诗文嬢嬢谑我父亲太严肃,学家父走路,惟妙惟肖,逗得全院笑。我这才注意到,家尊走路确实笔直,目不斜视。
依仁舅舅的家就在我父母打工的酱园店的街对面,我与次仁好,亦在其家偶遇到。李舅舅虽说乃川剧名丑,台上幽默滑稽,台下却少言语。但仅看他鹰钩鼻,瓦刀脸,八字眉,眯缝眼,说话不紧不慢,不时蹦句冷幽默,你若不笑,建议到医院瞧瞧,诊断是否痴呆了还是缺少艺术细胞。他演《滾灯》《柜中缘》《十五贯》,演谁像谁,活灵活现。甚至不用演,仅上台一站,不开腔,只“打望”,你先没懂名堂,忽恍然大悟,立马笑得眼泪迸出。而陈嬢嬢,我在《川剧缘》已有记言,的确是仪态万方美得心颤的好演员。
花钱看戏困难,那么,看古镇玩友“打围鼓”,就成了我的最大乐趣。打围鼓的场地多在老茶馆、印山公园以及城门洞的榕树坡坎。另外就是谁家有红白喜事也会请他们去“扎场子”,我定会同去听川剧。一帮玩友,文武场家什全有。围个圈圈,扯伸摆圆。胡琴一响,即算开场。往往是未见其人先闻锣鼓与笛声。再听高腔的高亢,胡琴的悠扬,灯戏的婉转,弹戏的清亮。而最摄人魂魄当属川戏的帮腔,演员叫声板,帮腔便拔地起,九曲十八弯,余音久不息。帮腔能很好展示环境,烘托气氛,表达人物心情。
川戏唱词唱腔皆优美,颇具文学性和民族情,且有教人向善的作用。你听魏明伦老师《杜兰朵》中的唱段:
“沉鱼落雁外貌美,岁月一摧满面灰;龙楼凤阁权势美,朝代一换黍离悲。清风明月自然美,天高海阔任鸟飞;真情挚爱心灵美,千秋万代映光辉。可叹我天之娇花之魁,娇生惯养耀武扬威。华而不实言而无信有何美?华而不实言而无信有何美?美在那不显山不露水,不自高不自卑,平平淡淡踏踏实实,一朵小花蕾……”
——这段内心独白,通过对比、反复和帮腔的烘托,在美的语言、美的唱腔中,潜移默化给人以哲理、以教育。
再听杜十娘倚船舱、翘首等夫的深情唱:
“夜色苍茫初更后,晚风吹来冷飕飕。手把船篷望江口,李郎不见我痴倚船头。夫妻们偕伉俪情深义厚,备美酒理寝枕等夫归舟”。
而李甲归舟心神不定,十娘猜夫心思尽显贤德人品:
“莫不是中途盘费不够?这一点小事妻早已运筹。莫不是风雪阻挡难行走,归心似箭便生忧?要不然妻有时言语错出口,冒犯你,妻来赔礼把罪求。再不然想求功名怕误时候?你有文才迟早朱衣会点头。
东猜西猜猜不透,我想个什么法儿去解李郎忧?”
——不用看深情款款的表演,仅欣赏曲调的婉转,浓郁的地域特点,不由你不沉浸里面,受其感染,挥泪长叹。
先君在世时亦喜川剧,我也是由他领着方正经看过几场戏。父亲不但爱看,还爱哼。哼的什么听不清,但瞧他闲坐桌边,微闭豹眼,轻扣指环,摇头晃脸,神情释然似神游九天,我就能判断那是老人极少见的最高兴不过的时候。
老家武胜县城比我大几岁的外侄汤诚与汤林,皆喜戏曲。“文革”来了,普及“样板戏”,广播天天放,以能唱为荣光。二侄儿不但能唱,京胡亦能拉,且拉得颇像样。当时汤林正下乡,大热天挑担粪去浇队上高粱,苦中作乐来一嗓:“青纱帐举红缨一望无际……”。声音回荡在田野里,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三
受环境熏陶,我亦迷上了戏曲。人有兴趣就是神奇:不识谱,却能唱得基本不走样;不懂程式,依电影招式也能学得有些模样。我很快入选小学宣传队,专演样板戏,且皆是英雄人物。譬如“鱼水情”中的郭建光,“赴宴斗鸠山”的李玉和,“定计”里的少剑波。当年古镇唱京剧者不多,故我受赞扬颇多。小学未毕业,即被“保送”进镇宣队,成其为最幼小的一位。
镇宣队全称是“中心镇宣传队”。它虽为业余团体,当年却大有名气。66年老戏禁演,川剧团解散,镇宣队员则是从各区乡遴选的文艺骨干,一些还是专业演员,谁能加入都觉风光无限。譬如乐队的周佑群,乃近四十的资深艺人,原本县剧团琴师头一名。他拉京胡,丝丝入扣,托着你走,让你随心所欲而不至于跑偏到哪里。
我的音是高,亦准,但板眼不稳——就是节奏差劲。加之我“不良”出身,且瘦骨嶙峋,扮相自然不如人。有人反映,说我的模样及出身,对英雄形象有折损。镇宣队孙队长,籍贯山东莱阳,三十郎当岁,瘦高健壮,常穿套绿军装,说话当当响:“奶奶个熊,嘛不像?不像谁像?谁都不像有俩疙瘩肉的钱浩亮,还不照样唱。小孩有吗罪?能唱成这样,就该表扬。咱得培养新生力量。”
而周佑群不但艺术水平高深,更是位忠厚人。用专业口吻,替我说情:“目前中心镇,比这娃儿唱得还像京剧的,恐怕莫得人”。
其实,参加镇宣队,也没啥大实惠。可在缺衣少食、出身又“违时”、老无端受歧视的当时,能侥幸加入宣传队这组织,唱戏听戏随你意,实在是我廉价的“穷欢喜”——它能暂时忘却境遇的不如意。可排练、演出皆为义务,无任何补助。唯一“待遇”是卸妆后,同去吃二两红油葱花面,算是夜半的加餐。就那面款还是全体队员挑竹篓挣的钱。说及挑竹篓,大概要算“搞特殊”:镇宣队承包,其他棒棒不准挑。力钱却归队里管,方便演后的付面款。竹篓乃外地订的榨菜篓或酒缸篓,由篾店师傅编,队员从无逸街起肩,挑至东门河滩上帆船。我人矮竹篓长,挑起直晃荡。挑担队伍如长线,在幽幽青石板街面极显眼。这几乎是镇宣队员最得意的“名片”,挑着它,惹得古镇男女青年全都刮目看。
四
1973年我新疆谋生,一度无法生存,几乎走进绝境。极度沮丧,倍感前途渺茫。是戏曲给了我生活的力量,能直面厄运,咬牙力扛。肚内“潮”得慌,就唱“我看那富贵荣华如粪土,穷苦人淡饭粗茶分外香”(京剧《红灯记》);困顿则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坚持在芦荡”“遮不住红太阳万丈光芒”(京剧《沙家浜》)。孤独绝望则唱:“我好比失群一飞鸟,我好比断线一风筝。矿山烈火烧不尽,我一颗红心被困在荒村”(京剧《节振国》)。现在想起着实滑稽,类似于阿Q的精神胜利。而遇时运不齐,内心压抑,戏曲的确给了我不少心灵慰藉,不至于一蹶不振,一败涂地。
“四人帮”灭亡,我考上了学堂。不久,政府提倡弘扬国学,传统戏曲得以繁荣。各种传统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影响最大当数越剧《红楼梦》黄梅戏《天仙配》京剧《铡美案》评剧《刘巧儿》昆曲《牡丹亭》等。国人争相观赏,几近万人空巷。
《红楼梦》票价三角,对我这每月仅有两元补助的师范生,不算小数目。可我不惜血本,连看了两场。边看边记还不够,晚自习竟翻墙出去,去露天影院外“听”戏曲。亦是边听边记,回宿舍再整理,以致花去我不少时间和精力。我却相当快意,乐此不疲。所以,像《红楼梦》《天仙配》,我能从头唱到尾,当然间杂麻辣味。自娱自乐,颇过瘾——戏曲真能陶冶性情,修炼人品,使你对民族文化产生感情,高雅素质得以提升。
戏曲唱段多,内涵丰富,旋律更独特。你就是请名主持人来念,也不一定能念出其中的韵味和美感。必须得唱。有的戏还必须用适宜剧种来演唱。譬如《牡丹亭》,杜丽娘初见自家后花园,欣喜无限。曲调得高雅,唱词得古典,得有名门闺秀的娇嗔羞赧: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这段就必须用昆曲。因那种高贵,那种典雅,那种历史的积淀,非昆曲的清丽舒缓、舞姿翩跹不能表现。此时此景,也只有昆曲才可展示江南少女的春情,才能演出戏曲的历史厚重,才能明白你我血液与别种血液的区别,才能懂得什么是华夏,什么是民族精华以及国粹文化的高雅在哪。而《白蛇传》,则最好京剧来演。开篇云雾弥漫,楼阁时隐时现,再听白娘子的梅派唱段:“驾彩云离却了峨眉仙山,人世间竟有这美丽的湖川……”,再后的“借伞”、“水漫金山”,非京剧难表现其大气和“有范儿”。那么,像《滚灯》《变脸》《迎贤店》《拜新年》,由川剧来演味道才具四川的麻辣鲜。
再后,有了工作,学校搞联欢,我的爱好又得以施展。所排节目送市、局,常得第一。1990年,和田市电视台亦开始搞春晚,年年拉上我,每到岁末,总在电视台度过。不仅演戏曲,还编排小品、朗读诗文,忙得不亦乐乎,但忙却快乐着。
五
1993年底,我要调至攀枝花。原因之一是那里有京剧、川剧、歌舞剧。各有其剧团,红火非一般。当年攀枝花的三个团水平皆高,星期天轮番演,让人流连。我几乎每场都看。不但自己看,还带学生看,还介绍剧团进校园。不但请来演,还请演员与学生座谈。有次座谈,领队的是市文化局副局长王海先生,来的全是京剧团大腕,阵容豪华空前。学生争相发言,会议室挤个爆满。应学生邀请,梅派名旦高枫就在会议室有限的空间歌舞《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东升。皓月当空,奴似嫦娥离月宫……”。高枫凌空起舞,长袖舒展,学生惊呼神奇,掌声不断。
看学生如此兴奋,我感到年轻一代对国粹艺术不是不能接受,也非觉得不好,关键是我们重视了多少,宣传了多少,自己又懂多少?倘自己一点都不懂,且毫无兴趣,还自以为“没关系”,何谈重视、宣传与发展?诚然,现而今不乏花大价钱去学琴棋书画的学生,但那基本属于急功近利、企图高考加分、把国粹文化当敲门砖而已。长此以往,国粹文化的弘扬恐怕就无望。而国粹文化的衰落,必将削弱国人内在特质,削弱民族凝聚力,致使国民素质下降,甚至道德品行沦丧。这里,我痛心于举例,就此转移话题。
事隔十年,市创评会相聚,王局长一眼认出:“哦,陈老师,多年不见”——戏曲让我们友谊没了时空的距离。是的,因为戏曲,我结交了攀枝花戏剧界不少朋友,如潘基安、普光泉、于映时、程尊堂、彭小龙、高枫以及众多票友。
不仅攀枝花,2013年的四月天,我去领全国戏剧文化奖,在浙江海门幸遇了众多大编导和梅花奖演员,真是“俊采星驰,胜友如云”。但我不想列举,怕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疑。而我在采风车上,总见位高个、精神,一路关照我们的帅气中年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先以为是导游,打听方知,人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电视艺术中心编导室主任、著名剧作家李东才先生。李老师说话细语轻声,笑容和蔼可亲。又因戏曲,我们聊在了一起,而且投脾气。认识虽仅三两天,却深感相见恨晚。东才老师的确具备大艺术家那种虚怀若谷的坦诚和谦逊。闲聊知晓,他写过《火热的心》、《孙中山与宋庆龄》等逾百件作品,得大奖无数次,令我肃然起敬。临别之际,李老师送我一盒他作词的光碟《舍不得你走》,作品情真,深沉感人。去年中秋,老师又来短信,说央视中秋晚会有他写的《秋花赞》戏歌,并应约把唱词发予我。写的是京剧名优程砚秋,也可说是写给所有戏曲从业者。词曲意切情深,古韵苍劲。那晚,是程派青衣李佩红来演,其声腔,幽咽婉转,若断若连;柔中带刚,荡气回肠,真是“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不敢独享,恭敬抄上,与读者共赏:
“凌霜花枝艳,一任秋光染。历尽沧桑俏依然,挺立百花川。根深深,意绵绵,生生世世芳菲恋。心欲翔,身如燕,烈舞悲歌满菊天。更馨香宜人风迷醉,大韵秋声岁岁酣……”
六
适才写作空档,倚沙发冥想。朦胧来一梦,似乎在我中学班主任詹世英家作客。朋友甚多,忽见一倩影,乃川剧名伶沈铁梅,正与世英老师凉椅上摆龙门阵。我给铁梅寄过我在报刊发表的写她的文章,故曾有短信来往,铁梅亦托其秘书给我打过电话。但相互未见,亦没通语言。我是个想见又怕见名伶之人,战战兢兢,犹豫不定。铁梅转身,尽显陌生。我说我是寄拙文的教书匠人。她方明眸晶莹,有了热忱。屋内太挤,示意我出去。外面,是山水的翠绿和新鲜的空气。正欲开言,梦已阑珊——窗外的高楼,美轮美奂。
短信响,是昔日的周村班长。说,昨晚与夫君去看铁梅的戏,把我的文集送到了铁梅那里。
下面写的并非梦:2013年四川散文学会搞首届纯散文评比,市文联鼓动我参与。我知晓我的斤两,而世上许多事,“怂恿”作用不可估量。便答应将我的杂集《陈文老酒》随市文联统一寄了去。与奖无缘是肯定的,却有幸结识了位不曾蒙面的戏剧挚友——万郁文老师,她是《四川散文》的副总编辑。万老师热情好义,或许是从我书中知晓我喜好戏曲,猛给我鼓励,将我的《川剧缘》发表在《四川散文》2013年第五期。我去短信感激,方知非川籍的郁文老师竟是位川戏迷。偶或给我发些剧照和蓉城演戏的消息,令我甚为欣喜。然远隔千里,晓得信息亦是“空欢喜”。而万老师仍旧发,就像她的同事晓荷编辑的美文中所写的,“与郁文交际,有种被阳光青睐”的惬意。郁文老师说得好,“如今欣赏戏曲者相对较少,我们该为她的传承增添点火苗”——又是戏曲,增添了我俩的友谊。
我要高兴地告诉我的朋友们,现在,就连我处边城,也有了些喜欢戏曲的学生。今年我市三中艺术节,前天,2014年五月十三晚,高二14班的学生竟演出了京剧伴舞《梨花颂》,真有点梅派的华贵雍容。虽稚嫩难免,却是良好开端。孩子们唱得深情款款: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天生丽质难自弃,长恨一曲千古迷……”。
是啊,华夏戏曲就是带雨的梨花,天生丽质,娇艳无比,很需国人呵护和珍惜。切莫等她失去了,再悔极来段“长恨一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