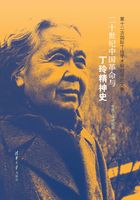
二
文艺大众化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这正如丁玲在《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的《编后》中所说:“文学大众化应如何实践的问题,是现阶段文学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因此,丁玲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贡献,不但在于其对文艺大众化理论的认知和探索上,更在于其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践行上。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以下简称“1930年决议”)在论及如何使文学“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时,提到了“工农兵通信运动”“平民夜校”“工厂小报,壁报”等方法和途径。 1980年,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是这样例举左联组织的文艺大众化实践的,其中包括:“建立工人夜校,在工厂组织读报组、办墙报,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等
1980年,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是这样例举左联组织的文艺大众化实践的,其中包括:“建立工人夜校,在工厂组织读报组、办墙报,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等 。所有这些,都曾经是丁玲所身体力行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所有这些,都曾经是丁玲所身体力行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和壁报运动。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不但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的“切实的实行”还曾被瞿秋白视作是“要开始经过大众文艺来实行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目前首重的任务”之一,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作家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决心”(见“1930年决议”)。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目前首重的任务”之一,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作家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决心”(见“1930年决议”)。
为了在工人中开展通信员运动,作为一个左翼作家,丁玲此期积极响应左联的“到工厂到农村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的号召,“换上布旗袍,平底鞋”深入到工人中去,“到跟自己有联系的工人家去坐一坐”、去“了解工人生活,和工人交朋友”。 数年之后,丁玲于1937年5月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海伦·斯诺采访时,还说到“那两年是我最快乐的时期”,因为那时她“每星期去访问一次工人”,她与工人“真的相识”了——通过和工人的谈话,她了解了他们的生活、 “性格”、他们身上的“革命的潜力”与“老是乐于领导任何运动”的革命品质;在这过程中,她还为那个“能写”的工人“修改过他几篇稿子”
数年之后,丁玲于1937年5月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海伦·斯诺采访时,还说到“那两年是我最快乐的时期”,因为那时她“每星期去访问一次工人”,她与工人“真的相识”了——通过和工人的谈话,她了解了他们的生活、 “性格”、他们身上的“革命的潜力”与“老是乐于领导任何运动”的革命品质;在这过程中,她还为那个“能写”的工人“修改过他几篇稿子”![丁玲语,见 [美]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264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B00D2/15367253104216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51709472-E8QmJPod3bh4k8F0tm8hnevH6ke4aNTk-0-4e4b49685afc366e5fa946ffab430b30) ,贯彻了“左联”在工人中培养通信员的宗旨。凭着自己在深入工人、开展通信员运动方面这些认识和积累,丁玲于1931年5月创作了短篇小说《一天》。作品的中心事件即为大学生陆祥为了开展通信运动而采访工人。他为了“一种信仰”,来到沪西区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白天,他走访工人,收集“压迫和反抗的铁证”;夜里,则“在黄的电灯光底下”,“用文艺的体裁”撰写通信。《一天》所写,正是“左联”所期待的“通信员运动”如何“促进作家到工厂当中去”的一个侧面,其中,在主人公身上也晃动着丁玲本人深入工人生活的影子、凝聚着丁玲本人深入工人生活的体验。
,贯彻了“左联”在工人中培养通信员的宗旨。凭着自己在深入工人、开展通信员运动方面这些认识和积累,丁玲于1931年5月创作了短篇小说《一天》。作品的中心事件即为大学生陆祥为了开展通信运动而采访工人。他为了“一种信仰”,来到沪西区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白天,他走访工人,收集“压迫和反抗的铁证”;夜里,则“在黄的电灯光底下”,“用文艺的体裁”撰写通信。《一天》所写,正是“左联”所期待的“通信员运动”如何“促进作家到工厂当中去”的一个侧面,其中,在主人公身上也晃动着丁玲本人深入工人生活的影子、凝聚着丁玲本人深入工人生活的体验。
为了促进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开展,丁玲不但自己亲力亲为,而且作为“左联”领导还发挥了其组织作用。为了培养工人通信员,“左联”建立了工人夜校,“为工人组织读书班,尤其在杨树浦”; “教他们读和写”,成了“我们那时的重要工作”![丁玲语,见 [美]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263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B00D2/15367253104216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51709472-E8QmJPod3bh4k8F0tm8hnevH6ke4aNTk-0-4e4b49685afc366e5fa946ffab430b30) 。艾芜当时参加文艺大众化运动,主要就是通过办工人夜校开展工作的。而艾芜的这一工作则是由丁玲直接安排的。1932年夏天,艾芜被分配到丁玲任领导的“左联”小组。在小组会上,“丁玲要我去杨树浦工人区域工作”,到男女工人补习学校(即夜校)教书,为的是“在男女工人中,培养出一批能写作品的所谓文艺通信员”;他“有时邀约几个人(指工人作者——引者),在虹口公园的草地上开会,丁玲曾来出席过,作过指示”。
。艾芜当时参加文艺大众化运动,主要就是通过办工人夜校开展工作的。而艾芜的这一工作则是由丁玲直接安排的。1932年夏天,艾芜被分配到丁玲任领导的“左联”小组。在小组会上,“丁玲要我去杨树浦工人区域工作”,到男女工人补习学校(即夜校)教书,为的是“在男女工人中,培养出一批能写作品的所谓文艺通信员”;他“有时邀约几个人(指工人作者——引者),在虹口公园的草地上开会,丁玲曾来出席过,作过指示”。 与此同时,丁玲还代表组织安排“左联”另一名盟员风斯(刘芳松)“到杨树浦担任组织工人通讯员的工作”,其后他的组织关系也被转到沪东区一个支部。
与此同时,丁玲还代表组织安排“左联”另一名盟员风斯(刘芳松)“到杨树浦担任组织工人通讯员的工作”,其后他的组织关系也被转到沪东区一个支部。
“左联”在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的同时,还积极倡导“壁报运动”(含“壁小说”又曰“墙头小说”)。这一运动的特点是:“它要求写得短而通俗,便于读者在极短的时间里看完。” 虽然看起来它的着眼点是在作品的形式,但同时还涉及到文学创作主体的培养、文学接受群体的设定以及文学社会价值的阐扬等重大问题。丁玲正是从“作品是属于大众”的认知和“文学的社会价值”出发,对这一运动作出了高度评价。在1932年冬所作的《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她写道:“左翼文学在许多地方像街头一篇墙头小说,或工厂一张壁报,只要真的能够组织起广大的群众,那末,价值就大,并不一定像胡秋原之流,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以外,还要求着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
虽然看起来它的着眼点是在作品的形式,但同时还涉及到文学创作主体的培养、文学接受群体的设定以及文学社会价值的阐扬等重大问题。丁玲正是从“作品是属于大众”的认知和“文学的社会价值”出发,对这一运动作出了高度评价。在1932年冬所作的《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她写道:“左翼文学在许多地方像街头一篇墙头小说,或工厂一张壁报,只要真的能够组织起广大的群众,那末,价值就大,并不一定像胡秋原之流,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以外,还要求着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
为了助推这种以大众为创作主体与接受群体、并具有其重大“社会价值”的“壁报运动”,丁玲在《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上刊出了工人作者白苇的《夫妇》和《墙头三部曲》这两组“墙头小说”。前者以副标题“墙头小说四篇”(实有《夫妇》《在厂门口》《传单》《早饭》《传令的人》五篇)标明了其性质。这组小说所写对象均为工人,着重表现的是他们艰辛的生活和英勇的斗争。如《夫妇》中写到,三姐和丈夫两人一做夜工、一做日工,“除了礼拜以外,他们是没有见面的机会的”。《在厂门口》叙写曾经经受过失业之苦的工人——“他”后来又做了“罢工委员长”,领导工人罢工,最后壮烈牺牲。后者包括“分离”“流荡”“回转”三章。如标题所示,这也是一组墙头小说。与前者一样,后者每章篇幅也都很短小。不同的是,后者在书写对象和内容上却有其连贯性:第一章写主人公“小龙”在“五卅”事件的刺激下,去“离太阳顶近”的南方参加革命;第二章写“小龙”更名“应龙”从军,参加“革命战争”,后因“官长和兵士的利益冲突”,他离开军队回到上海,当“一个革命的民众”;第三章写他回上海后又更名“叔达”,进了一个工厂。这显然是作者以“墙头小说”形式表现较为复杂内容的一种尝试。在同期《编后》中,丁玲对这两组墙头小说和它们的作者作了“特别推荐”,称作者“如果是在正确的路线上发展,……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总之,从这两组墙头小说从“街头”移至“纸面”的刊出中,尤其是从丁玲对它们的“特别推荐”中,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对“壁报运动”(“墙头小说”)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
二、培养以“工农兵作家”为重心的“青年群众作家”。左联发起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和壁报运动,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从封锁了的地下层培养工人农民的作家”(见前述“1930年决议”)“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读者和拥护者”、并“促成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与指导者的产生”(见“1931年决议”)。作为“左联”机关刊物的主编,丁玲忠实贯彻“左联”的相关决议、积极参与和支持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和壁报运动,其立足点自然也主要在于培养文学新人(特别是其中的工农兵作家)。
丁玲自陈,其办《北斗》的“一条经验”就是“注重新人新作”,它“从创刊时起,大概就给人一个印象:既有老作家,又有新面孔” 。创刊号在“小说”栏中刊载了三篇小说,其中第二篇《祖母》的作者便是新人“李素”。而从“左联”1931年冬组织文艺大众化问题第二次讨论以后,丁玲更是在《北斗》上较多地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新作。其中有:风斯的《太阳向我来》(第1卷第3期,1931年11月),石霞的《无题》、耶林的《村中》和高植的《漂流》(第1卷第4期,1931年12月),李辉英的《最后一课》、匡庐的《水灾》和芦焚的《请愿正篇》《失丢了太阳的人》(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葛琴的《总退却》和文君(杨之华)的《豆腐阿姐》(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白苇的《夫妇》《墙头三部曲》、慧中的《米》、戴叔周的《前线通信》和莪伽(艾青)的《会合》(“目录”中题为《东方部的会合》)(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等。
。创刊号在“小说”栏中刊载了三篇小说,其中第二篇《祖母》的作者便是新人“李素”。而从“左联”1931年冬组织文艺大众化问题第二次讨论以后,丁玲更是在《北斗》上较多地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新作。其中有:风斯的《太阳向我来》(第1卷第3期,1931年11月),石霞的《无题》、耶林的《村中》和高植的《漂流》(第1卷第4期,1931年12月),李辉英的《最后一课》、匡庐的《水灾》和芦焚的《请愿正篇》《失丢了太阳的人》(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葛琴的《总退却》和文君(杨之华)的《豆腐阿姐》(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白苇的《夫妇》《墙头三部曲》、慧中的《米》、戴叔周的《前线通信》和莪伽(艾青)的《会合》(“目录”中题为《东方部的会合》)(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等。
上述新人作品的刊出,大体有两个路径:一是新人自己的投稿;二是丁玲的征稿。如石霞、高植、李辉英、芦焚、艾青等属于前者。李辉英出生于东北吉林,当时就读于吴淞中国公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怀着国恨家仇,“开始写些反日的文字,意在报复” 。《最后一课》是他的处女作,投寄给《北斗》后,很快便被刊出。艾青当时在巴黎,在看到《北斗》对待新人的态度后也寄来了他的诗作。耶林、葛琴等则属于后者。耶林曾以“E.L.”的笔名致信丁玲,向她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因耶林的通信处不详,丁玲在《北斗》第1卷第2期以“代邮”的形式公开作复,并向他约稿:“我希望你的稿子,别人的稿子,我所希望能看到的稿子,能快点寄来。”耶林见信后寄来稿件,这就是在第1卷第4期上发表的《村中》。葛琴回忆说:“我写小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开始的、那在 ‘一·二八’之后,丁玲先生编《北斗》时候。有一天她给我一封普遍征稿信……当时我十分不安,自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写,……但更苦的是从未接到过这样的信,好像不写就不好意思再看见她。所以苦思结果,我选了士兵这一范围的。”可见,葛琴创作《总退却》也是丁玲直接组织、催生的结果。
。《最后一课》是他的处女作,投寄给《北斗》后,很快便被刊出。艾青当时在巴黎,在看到《北斗》对待新人的态度后也寄来了他的诗作。耶林、葛琴等则属于后者。耶林曾以“E.L.”的笔名致信丁玲,向她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因耶林的通信处不详,丁玲在《北斗》第1卷第2期以“代邮”的形式公开作复,并向他约稿:“我希望你的稿子,别人的稿子,我所希望能看到的稿子,能快点寄来。”耶林见信后寄来稿件,这就是在第1卷第4期上发表的《村中》。葛琴回忆说:“我写小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开始的、那在 ‘一·二八’之后,丁玲先生编《北斗》时候。有一天她给我一封普遍征稿信……当时我十分不安,自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写,……但更苦的是从未接到过这样的信,好像不写就不好意思再看见她。所以苦思结果,我选了士兵这一范围的。”可见,葛琴创作《总退却》也是丁玲直接组织、催生的结果。
总之,不管是投稿还是征稿,从这些新人稿件的最后录用中,均可看出主编丁玲对他们的重视。不但如此,丁玲还多次在《编后》中重点推介了这些新人新作——这更是体现了丁玲对他们的培养和提携。对于石霞、耶林、高植等三人,她指出,这三个作者“除了高植似乎在什么刊物上见到过,其余两个名字,我相信都还是生疏的”,但是,他们的这三篇小说,在题材上“都非常有可取的地方”,“在意识上,也确有很好的倾向”。对于创作了那“两篇以上海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的葛琴、文君,丁玲作了“特别绍介”,不仅因为这两篇作品具有“纪念今年的五月”的意义,还因为它们的作者“是第一次发表作品”;她还表示“以后我们准备多多登载新从事写作的人的作品”。对于白苇、慧中、戴叔周,丁玲虽然指出了其新作“很幼稚”“还说不上好”,但是,因其特殊的身份(他们分别是“拉石滚修筑马路的工人”“努力于工农化教育工作而生活在他们之中”的教育工作者和“从工厂走向军营的炮兵”),她对他们还是作了“特别推荐”。
此外,对于那些投寄过稿件的青年作者,不管其作品是否刊用,丁玲还常常回信,并在有条件时召集他们进行座谈。金丁回忆,他的“稿子寄给丁玲,她是看了就回信的,而且信写得恳切,有说服力”,而“蒋光慈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 对投寄过稿件的工人作者“阿涛”,丁玲也随即回信。因为信被退回,丁玲特地在《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上发表《代邮》一文,再次作复。信中,丁玲对他的文章作了评点,在指出其作缺点的同时,高度肯定其“能够抓住反帝的工人罢工斗争做题材”,有“实在经验”,并鼓励他“更努力下去”。在以信函联系青年作者的同时,丁玲还召开过多次青年读者座谈会。其实,这些参加座谈会的青年“读者”却往往同时也是给《北斗》投寄过作品的作者,因而,从这类座谈会的召开中,不但可以看出丁玲对读者意见的重视,而且更可以看出丁玲培养青年作者的苦心。据艾芜回忆,1931年冬,他向《北斗》投寄过稿件,未能刊用,但很快收到了《北斗》编辑部召开读者座谈会的通知。“编辑部的主人,除丁玲而外,还有郑伯奇、冯雪峰、叶以群”,而“参加的读者只有三人,李辉英、朱爱华和我”。
对投寄过稿件的工人作者“阿涛”,丁玲也随即回信。因为信被退回,丁玲特地在《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上发表《代邮》一文,再次作复。信中,丁玲对他的文章作了评点,在指出其作缺点的同时,高度肯定其“能够抓住反帝的工人罢工斗争做题材”,有“实在经验”,并鼓励他“更努力下去”。在以信函联系青年作者的同时,丁玲还召开过多次青年读者座谈会。其实,这些参加座谈会的青年“读者”却往往同时也是给《北斗》投寄过作品的作者,因而,从这类座谈会的召开中,不但可以看出丁玲对读者意见的重视,而且更可以看出丁玲培养青年作者的苦心。据艾芜回忆,1931年冬,他向《北斗》投寄过稿件,未能刊用,但很快收到了《北斗》编辑部召开读者座谈会的通知。“编辑部的主人,除丁玲而外,还有郑伯奇、冯雪峰、叶以群”,而“参加的读者只有三人,李辉英、朱爱华和我”。 以四名编者接待三名读者(作者),丁玲对青年作者的重视和培养于此也可见一斑了。在她的培养下,不少青年作者有了更大的发展。如李辉英在《北斗》发表《最后一课》后,又在丁玲的“授意”下,创作出了以“反日”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万宝山》。
以四名编者接待三名读者(作者),丁玲对青年作者的重视和培养于此也可见一斑了。在她的培养下,不少青年作者有了更大的发展。如李辉英在《北斗》发表《最后一课》后,又在丁玲的“授意”下,创作出了以“反日”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万宝山》。
对丁玲在《北斗》上刊载“包括工农群众作家在内”的“青年群众作家”的作品,冯雪峰当时就给予了高度肯定。在《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北斗》第2卷第2期)一文中,他说:“《北斗》杂志开始以较多的地位来登载这些青年群众作家的作品,这是十分正当的态度。……我以为一切的我们的杂志,都应当尊重这样的作品和作家,每期都应当介绍一二个这样的作家。”自然,在《北斗》推介的这些新人中,就“作者的阶级”来说,有不少“似乎都还是大学生”(丁玲:《编后》,第1卷第4期),但是,他们却都是“跟着一种新的文艺运动而产生的”。这样,推介这些作者,也就是在助推“新的文艺运动”。当然,为了发展“新的文艺运动”,还是要以“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及指导者”为终极目标。正是在这意义上,冯雪峰在“造了 ‘青年群众作家’这名词”的同时,还特别点出其中“当然要包括工农群众作家在内”。
丁玲在《北斗》刊载“青年群众作家”的创作也内含着这一思路。她最初发表的大多是知识分子作者的作品,后来则较多地直接地推出工农兵作者的作品(如第2卷第1期上的工人作者匡庐的小说《水灾》 和终刊号上的三个工农兵作者的小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在推出“青年群众作家”时不断向后者倾斜、聚焦的过程。这既体现了“左联”“1930年决议”将“左联”“这个组织基础的重心应该移到青年群众身上,渐次转移到工农身上”的要求,也可见出丁玲培养工农兵作者的用心。
和终刊号上的三个工农兵作者的小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在推出“青年群众作家”时不断向后者倾斜、聚焦的过程。这既体现了“左联”“1930年决议”将“左联”“这个组织基础的重心应该移到青年群众身上,渐次转移到工农身上”的要求,也可见出丁玲培养工农兵作者的用心。
丁玲以“工农兵作家”为重心的“青年群众作家”的培养,是“在左联的明确指示下进行的”;她在《北斗》上发表“‘无名小卒’的作品”,并在《编后》里着意述及那些“被发现”的“工农兵作家”,是左联“‘提拔’和 ‘培养’普洛大众作家的具体体现”,也是她“落实决议(即 ‘1931年决议’)做的一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