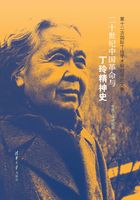
一
在20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中,丁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革命”相始终的历史人物。这不仅指作家活跃程度和创作时间之长,也指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了一种信念式的执著。从初登文坛的1920年代后期,到“流放者归来”的1980年代,丁玲一生三起三落,都与20世纪中国革命及其文艺体制的曲折历史过程关联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残酷地磨砺了她。丁玲生命中的荣衰毁誉,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不分彼此、紧密纠缠。
在她青春犹在的革命辉煌时代,她是革命的迷人化身。孙犁写道:“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不只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在她的晚年,革命衰落的年代,她是革命漫画式刻板面孔的化身。王蒙评价,她一生至死未解“革命”情意结,是一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
丁玲的一生,可以说活生生地演示20世纪中国不同的革命形态。1909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第二年,丁玲随湖湘“新女性”的母亲一同入读新式女校:31岁的母亲读预科,5岁的丁玲读幼稚班。那应是她革命生涯的开端。1984年,80岁高龄的丁玲雄心勃勃地创办了“新时期”第一份“民办公助”刊物《中国》。很多人对这一举动表示不解。李锐说:“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绝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丁玲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耗尽在这份新式刊物上。其间的77年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而走向革命政党的“螺丝钉”,从延安边区的明星作家、新政权文艺机构的核心组建者、新中国的文艺官员和多次政治批判运动中的受难者,到“新时期”不合时宜的“老左派”作家,丁玲不止用手中的笔,更用她的生命书写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20世纪称为“短促的”“革命的”世纪。他的纪年法主要以欧洲为依据,这个世纪只有77年。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历史比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要更长、更广阔、更深刻,也更复杂和更酷烈,以至费正清说,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形态,在现代中国都发生了。而丁玲,是(这些)革命的一个活的化身: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