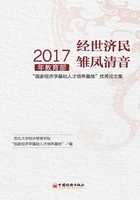
基于财政与货币交互机制的明代钞法考察与博弈论分析
李逸恺 梁义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明代钞法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将明代钞法置于财政货币体制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试图说明明代钞法的财政导向性、财政货币机制交互性两大特点,及其内在矛盾如何导致明代钞法最终崩溃,并运用博弈论进行分析。在当今货币发行与财政联系紧密、政府控制货币发行的制度下,如何处理好货币与财政二者的关系,明代钞法崩坏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关键词]明代钞法;财政货币体制;博弈论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明代钞法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当前学界对明代钞法的研究相对充分且成果丰富,涵盖钞法的缘起、内容、特点、实质、崩溃原因等诸多方面。乔晓金[1](1983)将大明宝钞的流通划分为稳定期、波动期、崩溃期和末期4个阶段,就明代钞币制度的特点及理论进行了探讨;唐文基[2](2000)通过对宝钞发行初期、贬值期、废用期3个阶段的梳理,指出宝钞政策的制定与出台是服务于国家财政需要而非立足于经济发展的考量,最终结果只能是官民受害,干扰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孙兵[3](2003)通过对洪武宝钞印造与支出的梳理,指出洪武皇帝实施钞法是以一种隐匿的方式达到聚敛财货的效果。黄阿明[4](2008)探讨了明代发钞的真实动机和目的,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大明宝钞的贬值、救钞手段及利弊。
大明宝钞的发行动机及实质与钞法最终崩溃密切相关,这是当前学界对明代钞法问题的共识。黄仁宇[5](1974)指出洪武皇帝大量发行宝钞的通货膨胀政策,实质上是为应付政府巨额财政支出的一种新的税收形式;王纪潮[6](1985)通过讨论大明宝钞废弛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封建社会国家发行货币是出于国家财政角度考虑而非基于社会市场的商品流通量,因而宝钞废弛是必然的结局;王玉祥[7](1997)通过对钞法内容、缺陷、敛钞手段、实施效果的考察,指出明朝实行钞法主要是为了聚敛财富,钞法的迅速崩坏与这种动机密切相关;陈昆、李志斌[8](2013)运用财政压力——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来剖析大明宝钞崩坏的制度根源,指出明代财政压力促成了宝钞制度设计,并最终导致货币超发、宝钞制度崩溃;张彬村[9](2015)运用现代的货币数量说和通货竞争、通货替代理论,从新的角度诠释了大明宝钞制度的崩溃原因。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觅得一条重要线索,即明代财政与货币两大经济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一方面,大明宝钞的发行以国家财政需求为导向,是一种财政型的货币制度和政策,宝钞过度发行源于政府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宝钞发行与回笼以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政策为形式,财政与钞法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过程。
在现有研究中,前人更多地集中在对大明宝钞制度缘起、内容、特点、实质、崩溃原因等的梳理,对该问题缺乏系统的讨论。陈昆、李志斌[10](2013)运用财政压力——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论证了明代财政压力对宝钞制度设计的促成作用,但缺乏对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交互作用的梳理;唐文基[11](2000)对宝钞通过财政支出单一渠道强制发行和通过增税、罚款等手段回笼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但对明代财政、钞法如何在统一目标下、统一系统内运作的考察仍显不足。且上述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材料整理与逻辑梳理,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则略显不足。
本文试图将明代的财政与钞法纳入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中进行分析,并提出如下假设:大明宝钞制度本身的财政性质以及明代的财政货币交互机制,是导致明代钞法崩溃的根本原因。本文着重考察了财政压力与宝钞制度的确立和货币与财政政策交互机制的运行,并建立了一个博弈论模型,以便为上述假设提供理论与事实层面的支持。
本文论证的框架如下:

其中,“+”表示正向促进作用,“-”表示负向抑制作用,“×”表示财政收入贬值风险对货币回笼政策的壅塞。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与文献综述,同时提出了本文的假设与逻辑框架;第二部分概述了明代钞法建立→危机→挽救→解体的过程;第三部分通过考察明朝初年国家财政状况,说明明代钞法的财政导向,即财政压力对宝钞制度确立与货币超发的促成作用;第四部分梳理宝钞发行与扩张、回笼与紧缩政策,指出明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互为表里、相互作用,其内在矛盾最终导致了大明宝钞制度的崩溃;第五部分运用博弈模型对明代钞法崩溃的原因作进一步说明;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明代钞法概述
元明之交,由于元朝纸币制度崩溃,各地恢复了铜钱流通,起义军建立的地方政权均曾铸造铜钱。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于洪武元年颁行洪武通宝钱制,铸造洪武通宝钱[12];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恢复建立了纸币流通制度[13]。
据《明史·食货志五·钱钞》所述,大明宝钞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几点:
(1)钞面以钱文计,宝钞分六等: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14],后来还曾加发五十文以下的小钞[15]。
(2)政府发钞不备金、银本钱,禁止民间私易金银,只允许人民持金、银向政府换易宝钞[16];金、银的法定官价是:钞一贯等于银一两,四贯等于金一两[17]。
(3)钱钞兼行,但铜钱支付能力有限。洪武十年规定:百文以下交易支付专用铜钱,而商税的输纳,则以钞七钱三为原则[18]。
(4)宝钞久用昏烂,军民商贾可持旧钞赴行用库换易新钞,政府量值收工墨费[19]。
与前朝纸币制度比较,大明宝钞制度具有以下特点:无发行准备金且不可兑换;大明宝钞形制为定制且始终未曾更改;纸币制度为钱钞兼用,纸币为主,铜钱为辅。
由于宝钞是政府强制发行的不可兑换纸币,且发行数量又无节制,日积日多,收少出多,流通中纸币充斥,宝钞贬值愈演愈烈,明初的纸币流通,仅二十年间便趋于败坏。彭信威(1943)在《中国货币史》中,对大明宝钞价值变化进行了系统整理(见表1),我们可以从中窥得大明宝钞前后价值变动。
表1 大明宝钞价格

续表

资料来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671-672.
根据表1绘制的折线图使我们得以更加直观地认识大明宝钞的贬值。
据表1、图1、图2可知,宝钞从一开始就持续贬值,且下跌不止,直至最终崩坏。

图1 大明宝钞兑钱价格

图2 大明宝钞兑银价格
为维护纸币制度,明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包括停用铜钱、申严金银之禁、实行“户口食盐法”,罚赃输钞,以至于添加各种苛税等货币回笼举措。但由于其禁用金银铜钱的命令未能得到有效贯彻,且以税收方式回笼纸币,依然是收少出多、增发不已,因而收效甚微。纸币贬值的趋势无法遏制,纸币流通范围更加缩小。孝宗弘治年间的钞关,钱、钞皆折银收取,纸币流通已然名存实亡,在经济生活中已无意义。明中叶以后,宝钞事实上已不行用,商业交易及民间日常支付均使用白银或铜钱,政府印钞发钞主要是作为保存祖制的一种象征性措施。
三、明代钞法之财政导向
《国朝典汇·钞法》中,对大明宝钞发行动机有所记载:
“洪武八年三月,诏造大明宝钞。时中书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铸钱,有司责民出铜,民间皆毁铜器输官鼓铸,甚劳,奸民多盗铸。又商贾转易,钱重道远,不便。上以宋有交会法,而元时亦尝造交钞,及中统至元宝钞易于流转,可以去鼓铸之害,遂诏中书省造之。”(1)
由此观之,太祖令中书省造大明宝钞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宝钞便于携带,利于流转,可以有效避免“钱重道远”的不便,促进商品交易与货币流通;二是可以有效避免“鼓铸之害”,在减轻铜器输官给百姓带来的负担的同时,有效抑制奸民盗铸现象。除以上原因外,明朝时下国库空虚、金银匮乏、财政窘迫对大明宝钞发行的作用更为关键,明太祖显然未曾明言。
明初,明太祖即指出:“以朕观之,宽民必先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故应“其赋重者,悉宜减也”(2)。据此,明朝实行了低税政策,田赋税率差异大,但总体赋税较低。据黄仁宇[20](1974)的统计,明代的税收与宋代相比明显偏低,按可比价值计算,明代每缗铜钱与一石粮食相抵。依据宋代记载,到11世纪中期,每年的预算已经达到12600万缗到15000万缗之间,而明代平均田赋仅有2700万石,我们可窥得其中的巨大差距。除此之外,明太祖重视田赋的减免。边俊杰(2011)据《明史·太祖本纪》不完全统计,明太祖在位期间曾40多次下令免除各地田租。各地如发生水旱等自然灾害,一律免除田租,对地瘠民贫者,经地方呈请减免一部分或大部分田赋。《明史·食货志》载:“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洪武时,勘灾既实,尽与蠲免。”(3)以上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明初低税收的基本事实。
明初的低税收与膨胀的财政支出需求形成了矛盾。对于明代的财政支出,唐文基[21](2000)、黄阿明[22](2008)、陈昆和李志斌[23](2013)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细梳理。将明朝财政支出分为经常性和临时性支出两类,经常性支出包括宫廷支出、宗室俸禄、官吏俸禄、军兵月盐和盐户工本,临时性支出包括赏赐文武官员、士兵、内外使者、工匠,以及赈灾、采购粮食、马匹等。其中,临时性支出占主要份额。宝钞被大量地用于军费支出和赈灾备荒支出。明初战事频繁,王朝对元朝残余和边远地区割据势力(如敦煌、云南、汉北等)的征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各地灾荒也都需要大量支钞。面对财政危机,政府发行不兑换性纸币显然是一种满足财政开支需求与缓解财政危机的手段。我们也可据此推知,明代钞法从建立之日起即带有明显的财政导向色彩。
明太祖统治期间又确立了税收定额制度。洪武十年,明太祖分遣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一百七十八个税课司局以固定其税收额度;洪武十八年,明太祖下令将各省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并树立在户部厅堂中;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宣布北方各省新开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被固定下来,后期虽有微调,但基本定额从未被摒弃。
明太祖虽然降低并固定了田赋,但国家职能却是刚性的,其财政需求不能因此减少或固定,这便形成了与年俱增的支出需求与固定的收入之间的矛盾。永乐年间军事行动仍然持续,明王朝征伐挞粗、瓦刺、安南,每次出兵都有数十万乃至百万之众;而规模巨大的营建工程更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永乐四年北京城开始营建,历时十五年才最终建成,其间动员的工人达一百万人,还从山西移民万余户。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营建两京“采木,陶凳工匠,造作”(4)耗费约亿万两,工程一直持续至洪熙、宣德年间[24],而当时政府每岁的财政收入仅有二百万两。明英宗朱祁镇两次登极,多大兴土木[25],且又有缅甸、土木之役,都极其耗费钱财。而明太祖的税收定额制度使政府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大的增长,两下相较,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可见一斑。
由于正常的税收不足以弥补支出,必要项目开支就要通过其他各种方式来解决。洪振快[26](2008)提出了“亚财政”的概念,即伴随正式财政制度变迁的非正式财政制度。最初民众负担的仅仅是“明税”,但随着政府财政压力不断扩大,民众承担的“税外之税”“赋外之赋”则越来越重,这就是所谓的“亚财政”。而大肆发行大明宝钞,其效果便是向民众征收通货膨胀税,是一种“亚财政”的手段。国家在无准备金的情况下发行宝钞,可以零成本获取大笔财富;宝钞金银单向兑换,用宝钞兑换民间金银,使国家的金银储备大增;同时,通过发行大明宝钞来隐蔽地获取财政收入,化解财政危机,百姓不易察觉,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圣君”形象和王朝统治。因此,尽管明洪武年间大明宝钞业已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且历朝君王中意识到钞法壅塞究其根源在于散出太多者也不乏其人,并采取了一系列货币回笼措施,但最终都未能克制继续增发宝钞的冲动,宝钞贬值非但未能被制止反而更加严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窥得,大明宝钞的发行并非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国家庞大的财政需求。大明宝钞诞生伊始即带有财政导向性,而该性质恰使以财政为国家经济政策中心的封建君主与专制政府,具有无限制发钞的激励,最终引发货币贬值、钞法崩溃。可以说,明代钞法的财政导向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最终失败。
四、明代钞法之财政货币交互机制
发行与回笼主要采取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手段,是明代钞法的显著特征。下文将考察这种财政货币交互机制的内在矛盾如何导致大明宝钞的持续贬值与明代钞法的最终崩溃。
大明宝钞主要以政府支出的方式流向市场。据上文所言,明代政府财政支出主要包括经常性支出与临时性支出两大类,与之对应的货币发行方式也包括经常性财政支出方式和临时性财政支出方式两类。其中经常性财政支出方式主要包括:
(1)宫廷支出。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为光禄寺用于祭、享、宴、劳、酒、醴、膳、馐的费用[27]。
(2)宗室俸禄。明朝宗室受封,男性受封亲王、郡王直至奉国中尉共六级,女性封公主至乡君共六级。受封宗室都要支取一定数额的宝钞[28]。
(3)官吏俸禄。宝钞发行后,洪武九年宣布,官吏俸禄以米、麦、钞兼支;洪武十八年又宣布文武官员以钞代禄米。
(4)军兵月盐。明朝前期采取征兵制和军户世袭制,规定按月另给军兵菜盐,又称月盐。军兵月盐部分或悉数折钞[29]。
(5)盐户工本。明朝沿续历代国家垄断食盐产销政策,给予盐户一定工本,收取盐户的产盐。洪武十六年令盐户工本米改领宝钞[30]。
除以上经常性财政支出方式外,使用宝钞赏赐文武官员、士兵、内外使者、工匠,以及赈灾、采购粮食马匹等,属于临时性财政支出方式。总而言之,大明宝钞的发行源于政府的财政需求,因而其发行方式也以财政支出为主要形式。
与之相似,明代的宝钞回笼政策,同样是以财政收入政策为手段达到紧缩货币的目的。
面对宝钞的严重贬值,当政者逐渐意识到个中原因。永乐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指出:“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5)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伊始,即向户部尚书夏元吉言:“钞法滞,盖由散出太多。宜设法广敛之,民间钞少,想自通。”(6)洪熙元年,夏元吉等讨论纸币问题时,也指出:“钞多则轻,少则重。朝廷敛散适中,则自无弊。今民间钞不通,盖缘朝廷散出太多。宜为法敛之。”(7)
在古代中国,紧缩货币的通常办法有二:一是增加商品投放量;二是以贵金属金、银回购宝钞。但明王朝手中既无足够商品可供投放,对后者又断然拒绝[31],最终选择以增加税种、税额和各式罚款的财政收入手段,以零成本达到货币回笼的目的,具体方式如下所述:
(1)征收“户口盐钞”。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建议“暂行户口食盐之法”,全国官民计口配盐纳钞,成祖准行。大口月配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折半,称为“盐钞”[32]。
(2)增收门摊税。门摊税即店面税,在明初业已存在[33]。洪熙元年下令增收门摊税四十倍。宣德元年以增收四十倍太重,降为增收五倍,并规定只在顺天、应天等府以及除云南、贵州之外的各行省中三十三个城市增收[34]。
(3)征收蔬地果园种植税。宣德四年六月,规定京师、南京军民种植蔬果贩卖者,蔬菜每月计亩纳钞,果树每岁计株纳钞[35]。八月,该税又推及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但税额稍减[36]。宣德六年又将蔬菜地种植税减半[37]。
(4)增收塌房、库房、店舍税。宣德四年六月始征,每间每月纳钞[38]。同年,对油坊、磨坊、砖瓦窑等征收数额不等税钞[39]。宣德六年以后,税额有所降低[40];正统四年塌房等税减半[41]。
(5)开征驴车、骡车运输税。宣德四年六月,规定凡受雇装载货物车辆,每辆依岁纳钞[42]。七月,还开征牛车、小车运输税[43]。
(6)设钞关,征船料。宣德四年六月,在从北京至南京的运河沿线的主要城镇都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和南京上新河设立七个钞关,征收船料[44]。
(7)罚钞。明代罚钞名目多样,如宣德元年十月,实施笞杖、流徙赎钞[45],同时又宣布罚钞赎脏例,金每两赎钞8万贯,银每两赎钞2000贯,铜、锡、铁、铅、纻丝、罗、棱、官棉布等各有赎钞标准。
以上财政收入政策,均是朝廷用以疏通钞法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在纸币回笼和收支平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黄阿明[46](2008)对此有详尽考证。但以上举措未能阻止大明宝钞的不断贬值,无法挽回钞法解体的命运。这与货币回笼政策以财政收入政策为其形式是分不开的,这种形式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其难以贯彻到底,失败具有必然性。
财政收入政策形式的货币回笼政策,天然便具有双重性质和功效,一方面致力于挽救宝钞贬值;另一方面是朝廷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宝钞贬值恰使国家面临财政收入贬值的风险。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钞法受国家财政状况影响较为严重。在财政紧张的状况下,朝廷为满足政府支出需求,又持续发行大明宝钞,这种边收边发、收少发多情况的最终结果,依然是流通中宝钞总量不断增长、宝钞不断贬值。而在宝钞贬值的情况下,若继续贯彻宝钞回收的货币紧缩政策,必将给国家财政状况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加大国家的财政金融风险。其原因在于,在政府没有任何预算盈余来保证宝钞币值稳定的情况下,宝钞不断贬值使得国家所掌控的货币实际价值远远低于其名义价值,以宝钞形式获取的赋税,在很大程度上面临成为毫无购买能力且不被社会所接纳的“废纸”,以宝钞形式获取的税收在总税收中所占的份额越大,财政所面临的贬值风险也就越大。这种风险使得财政收入形式的宝钞回笼政策很难长期贯彻下去。事实上,早在洪武时期,社会上虽严禁用银,但是为保障财政收入的实际价值,金银同样作为财政税收货币在缴纳。朝廷实则在以宝钞为法定支付手段的同时,还以金银为流通货币在征收赋税,且以金银征收赋税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增大,并最终将宝钞从税收支付手段中挤出。
综上所述,财政收入政策形式的货币回笼政策本身即面临巨大的矛盾。税收是国家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使用面临贬值风险的宝钞缴纳,很难保证宝钞能够在国家急用之时有效转化为具体实物,因此,国家很难将这一政策贯彻执行。选择收取价值稳定的白银或铜钱,是政府避免财政风险的合理选择。财政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货币回笼政策失效、大明宝钞贬值趋势难以有效遏制,明代钞法的最终崩溃也在所难免。
五、基于博弈论的明代钞法崩溃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纸币超发的囚徒困境
我们首先试图构建一个简单博弈模型,对政府滥发宝钞的原因进行分析。博弈的双方为政府与民众。在财政货币机制中,政府的核心目标有二:一为通过货币超发、征收通货膨胀税以获取财政收入;二为稳定宝钞制度以维持正常的经济交易秩序。其中,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动机要高于维持宝钞制度的动机,具有更小的成本和更大的收益。民众的目标同样有二:一为提高个人收入;二为避免个人财富缩水。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构建了如下2×2支付矩阵:

(1)政府滥发宝钞,民众拒绝接受宝钞进行交易。短期内政府可获得通货膨胀税,民众拒绝接受宝钞进行交易,可以防止宝钞贬值带来的财富损失,最终导致宝钞制度崩溃,支付为(1,1)。
(2)政府滥发宝钞,民众接受宝钞进行交易。一方面,政府获得通货膨胀税;另一方面,维系了宝钞制度,而民众则需要承担个人财产的不断缩水,支付为(4,-1)。
(3)政府不滥发宝钞,民众拒绝接受宝钞进行交易。民众认为政府不可信,预期宝钞贬值,引发物价上涨,生产者与商人可从中获益,同时也规避了个人财富缩水的风险,但政府需要承担宝钞制度崩溃的损失,支付为(-1,4)。
(4)政府不滥发宝钞,民众接受宝钞进行交易。政府无法获得通货膨胀税,但维持了宝钞制度和物价稳定,民众利用宝钞进行交易,同时避免了宝钞贬值带来的财富损失,支付为(3,3)。
综上所述,最后的纳什均衡是政府滥发宝钞,民众拒绝接受,宝钞进一步贬值,宝钞制度崩溃。政府滥发宝钞、民众拒绝使用、宝钞制度崩溃,形成一个囚徒困境。
那么,是否存在机制能使政府和民众走出纸币超发的囚徒困境呢?事实上,各朝统治均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尤其是在明代前期与中期,社会相对安定,矛盾并不突出,统治者和民众对王朝延续具有较强的预期,这一博弈更接近于无限期重复博弈。通常情况下,当贴现因子较大时,在冷酷策略下,双方是有激励维持合作的。我们假定贴现因子为δ,双方均采取冷酷策略,即一旦在任何一轮博弈任何一方选择背叛,对方即采取冷酷策略,合作就此瓦解。使冷酷策略有效的贴现因子需满足以下条件:

但事实上,中国历代纸币制度的最终结果通常是王朝滥发纸币、宝钞制度崩溃。
问题在于,对于政府而言,面对现实中边境少数民族的威胁、自然灾害救济和君主个人享乐需要,对缓解短期财政压力的诉求远远高于对维持宝钞制度的重视。同时,明代专制集权强化,滥发货币除了导致钞法崩溃外,由于存在铸币、金银等作为替代品,钞法崩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民众的直接伤害较为隐蔽,也不会导致经济的剧烈动荡,不易激发民变。因此,政府对未来钞法崩溃的担忧远远小于对当前边患、自然灾害和个人享乐所引发的财政危机的担忧。因此,这一贴现因子δ足够小,未来更加不被重视,合作必然难以维持。最终结果依然是政府滥发宝钞、民众拒绝接受、宝钞进一步贬值、宝钞制度崩溃。这是一个难以走出的囚徒困境。
(二)宝钞回笼政策的失败:一个博弈模型
1. 单次博弈
为了稳定币值,明政府试图以税收为手段达到回笼货币的目的,部分税收需以宝钞形式缴纳。这就使得超发纸币对政府财政收入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超发货币使政府获得通货膨胀税;另一方面,超发纸币引发的通货膨胀也将导致政府以宝钞形式征收的这部分税收贬值,带来税收损失。本部分在第一部分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将政府超发纸币带来的税收损失纳入考察,通过构造博弈模型进一步解释明代钞法的崩溃。
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政府关心的核心目标是最大化长期政府财政收入和稳定宝钞制度,其中,获取财政收入的动机高于维持宝钞制度的动机。政府财政收入由两部分组成:正常的税收收入和通过超发货币获得的通货膨胀税。明代早期的税制规定,上缴的税款须部分以金属货币和实物的形式上缴,部分以宝钞的形式上缴。因此,过度的通货膨胀势必导致正常税收收入的损失。明朝的统治者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朝廷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将宝钞从税收支付手段中去除以消除通货膨胀对税收收入的不利影响,但税制改革也会导致民众对宝钞彻底失去信心,因为此时超发货币对政府再无负面作用。
相对而言,民众关心的目标则比较简单。提高个人收入、避免个人财富缩水是普通百姓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民众可以选择相信政府发行的宝钞,接受和使用宝钞作为支付手段,但如果政府超发货币,民众的财产将会严重缩水。另一方面,民众也可以选择不相信宝钞,在平常的交易中使用实物交换或金属货币、抵制宝钞,这样将会避免财产缩水的风险,但抵制宝钞也会造成额外的成本,如交易成本的增加或公然抵制政府法定货币面临的惩罚等。

图3 模型的博弈树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建立了一个博弈模型,对明代宝钞制度的维持和崩溃过程加以简要说明。该博弈共分为3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政府设定宝钞的贬值率,即政府希望宝钞贬值的程度。根据设定的贬值率,政府可以确定超发货币的数量。货币的超发将以通货膨胀税的形式剥夺民众的个人财产。宝钞的发行量越大,贬值幅度就越大,通货膨胀税带来的政府收入也就越多。
这里,我们采用期末与期初每贯宝钞值银钱数的比值作为贬值率的度量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时期末的一贯宝钞实际上只相当于时期初的x贯宝钞,则贬值率等于x。例如,洪武九年一贯宝钞值一两银,而洪武十九年一贯宝钞仅值0.2两银,所以这一时期内的宝钞贬值率为0.2。鉴于大明宝钞几乎一直在发生持续的通货膨胀,我们设贬值率q为[0,1]内的一个数值,其中q越小则表明通货膨胀情况越严重。由于时期末宝钞发生了贬值,民众的财富也相应地缩减到了原先的q倍,因此,政府通过超额发行货币征收了数额为1-q的通货膨胀税。
在第二阶段中,民众可以设定预期宝钞贬值率,也即市场中实际的宝钞贬值程度。在政府作出货币发行决策之后,民众不可能立刻了解货币的发行情况,而只能根据经验进行猜测和估计。民众整体的预期将影响宝钞的实际购买力。如果民众普遍相信宝钞没有超发,非常乐于按照原先价值接受宝钞,则短期内宝钞的购买力将不会发生剧烈变化。而如果民众对宝钞普遍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拒绝接受和使用宝钞,那么宝钞的贬值速度将快于政府设定的贬值率,导致宝钞购买力严重下降。这种预期效应将具体在民间市场中宝钞与金属货币的兑换价格中体现出来。
模型中,我们利用和贬值率相近的方式设定民众预期贬值率qe,即民众认为时期内宝钞会发生的贬值幅度。类似的,我们设定qe为[0,1]内的一个数值。若qe=1,即民众愿意按面值接受宝钞,则民众时期末将受到政府超发货币的影响,效用为q。若qe<1,即民众对宝钞表示不信任、拒绝按面值接受宝钞,而只愿意以价格qe接受1单位宝钞,此时民众的财富缩水程度将被减轻为q/qe,但这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和对抗政府的成本c。为了使模型更加合理,我们规定q/qe≤1(预期调整本身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效用)。综上,qe<1时,民众的效用为 。
。
在第三阶段中,政府可以决定是否进行税制改革。政府可以观察到宝钞此时的实际购买力qe,据此决定是否仍然继续设定税额部分由宝钞形式缴纳。继续接受宝钞为税收支付手段将导致税收收入受到影响。而如果进行税制改革,规定全部税收均需以实物形式上缴,会提高当期税收收入,但会使民众严重丧失对宝钞体系的信心,影响下一阶段中民众对宝钞贬值情况的预期。
政府在这一阶段中有两个选择:改革R和不改革N。设额定税收收入为t,若进行改革,则确实获得税收收入t;若不进行税收改革,则以宝钞形式支付的税赋将发生贬值。我们不妨以商税钞七钱三为参考,则税收收入为0.3t+0.7qet。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支付(政府设定贬值率为q∈[0,1],民众预期贬值率为qe∈[0,1],政府选择改革R/不改革N):
(1)民众相信宝钞(qe=1),政府不进行税收改革:(1-q+t,q);
(2)民众相信宝钞,政府进行税收改革:(1-q+t,q);
(3)民众不相信宝钞,政府不进行税收改革: ;
;
(4)民众不相信宝钞,政府进行税收改革: 。
。
通过支付函数我们可以发现,设定q=0和进行税收改革是政府的弱优势策略。此时,民众的最优反应是qe=0,双方的效用为(1+t,1-c)。也就是说,单期博弈中的纳什均衡是政府进行恶性通货膨胀获得最大程度的通货膨胀税,同时进行税收改革保证税收收入不贬值,民众则完全不相信宝钞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个人财产损失。
2. 无限期重复博弈
前文已经指出,由于朝代内部的政策具有延续性,政府的目标也是最大化长期财政收入,尤其是在明代前期与中期社会相对安定、统治者和民众对王朝延续具有较强预期的情况下,该博弈更接近于无限期重复博弈,而非单次博弈。
将上述博弈转化为无限期重复博弈几乎不会对模型设定产生影响。一个需要修正的细节是,当政府设定的贬值率与民众预期贬值率不一致时(即 时),流通中的宝钞的名义总量变为1/q1,实际总购买力变为
时),流通中的宝钞的名义总量变为1/q1,实际总购买力变为 ,此时再设定下一期期初的宝钞实际总量为1就不太合适了。也就是说,民众的预期造成宝钞的购买力与实际发行量发生了偏差(实物和金属货币升值或贬值了),在继续发行宝钞时,实际的贬值效果会受到这种偏差的影响。例如,政府可能在某时期内设定贬值率目标为0.5,并开始超发货币。在正常情况下,货币发行量需提高一倍才可以达到这一目标。但由于民众在前一时期内已经不再以面额接受宝钞,宝钞的购买力将更快地下降,使政府在将货币发行量提高一倍之前即达成贬值率目标,从而削弱了通货膨胀税的实际效力。
,此时再设定下一期期初的宝钞实际总量为1就不太合适了。也就是说,民众的预期造成宝钞的购买力与实际发行量发生了偏差(实物和金属货币升值或贬值了),在继续发行宝钞时,实际的贬值效果会受到这种偏差的影响。例如,政府可能在某时期内设定贬值率目标为0.5,并开始超发货币。在正常情况下,货币发行量需提高一倍才可以达到这一目标。但由于民众在前一时期内已经不再以面额接受宝钞,宝钞的购买力将更快地下降,使政府在将货币发行量提高一倍之前即达成贬值率目标,从而削弱了通货膨胀税的实际效力。
经过计算可得贬值效果 与政府设定贬值率q2之间的关系:
与政府设定贬值率q2之间的关系: 。这种偏差将会影响政府的通货膨胀税——民众的预期宝钞的贬值情况越严重,通货膨胀税的效果就越差。这样,1-qn/An就是第n期博弈的通货膨胀税(8),An项与民众的预期贬值率成正比。支付的其他部分(民众的财富状况及政府税收收入)没有受到影响,因而将上述支付表达式中的1-q替换成1-qn/An,即第n期双方的支付。
。这种偏差将会影响政府的通货膨胀税——民众的预期宝钞的贬值情况越严重,通货膨胀税的效果就越差。这样,1-qn/An就是第n期博弈的通货膨胀税(8),An项与民众的预期贬值率成正比。支付的其他部分(民众的财富状况及政府税收收入)没有受到影响,因而将上述支付表达式中的1-q替换成1-qn/An,即第n期双方的支付。
如果政府进行恶性通货膨胀、采取税收改革,民众将会完全失去对宝钞的信任,宝钞体系将于下一时期彻底崩溃,博弈结束。但在长期利益的驱使下,政府将选择不进行税制改革,以避免民众对宝钞体系丧失信心,同时设定贬值率q以使得qe=1,令民众相信宝钞体系。也就是说,令 。因此,冷酷策略下的合作均衡为q=1-c,qe=1,不进行税制改革,此时双方的长期收益为[(c+t)/(1-δ),(1-c)/(1-δ)]。
。因此,冷酷策略下的合作均衡为q=1-c,qe=1,不进行税制改革,此时双方的长期收益为[(c+t)/(1-δ),(1-c)/(1-δ)]。
通过这一均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当贴现因子不是太小时,在冷酷策略下双方是有激励维持合作的。合作均衡中,民众将忍耐政府进行的相对较温和的货币超发,且双方的福利水平与金属货币的交易成本和政府对于不使用法定货币的惩罚力度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实际上,这种均衡并不能长期维持,最终的结果通常是王朝滥发纸币、宝钞制度崩溃。
如上一部分所分析的那样,政府对未来的担忧远远小于对当前边患、灾害和个人享乐的财政危机的担忧。因此,当这一贴现因子δ足够小时,合作必然难以维持。而一旦民众对宝钞制度丧失信心,想要恢复民众的信心就十分困难。最终结果依然是政府滥发宝钞,民众拒绝接受,宝钞进一步贬值,最终导致宝钞制度崩溃。
六、结论
国家财政是国家运用其政治、财产的权力,取得、分配和使用一部分社会资源,为实现其职能服务的资源配置行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取得、使用、分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关乎国家职能的顺利实现,也关乎社会各阶层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而货币作为商品经济的“润滑剂”,对商品流通与经济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既相互关联同时又存在内在矛盾冲突,本文正是将明代钞法纳入财政与货币交互机制中去考察,以期获得关于财政货币体制的一般性规律。
通过考察明代钞法建立→危机→挽救→解体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窥得中国古代纸币制度中所含规律。中国古代纸币发行由国家控制,政府常常会忽略货币流通规律,选择滥发纸币作为化解财政危机的手段,而因此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会使政府财政陷入恶性循环、纸币体系壅塞崩坏,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财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中心。国家机器运行、国家职能行使都需要以财政收入为保障,以财政支出为手段。在中国古代的财政货币体系中,货币体系天然从属于财政体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财政需要。不独立的货币体系,使得强悍的封建君主与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去忽略和抛弃货币流通规律,以超发货币的方式满足财政需求。
今日中国,财政与货币体系的复杂性与封建社会绝不可同日而语,财政收支与货币供需受到更多、更加复杂的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财政收支与货币发行依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财政与货币交互机制依然存在并以不同形式发挥着其作用。同时,掌握国家货币发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下属机构,依然从属于政府,货币发行权依然被政府所掌控。一方面,这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货币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实现国家职能;另一方面,却更容易诱发政府的短视行为与财政冲动,危害经济社会稳定与长远发展。处理好财政体系与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建立更加独立、规范的货币发行机制,强化货币供给约束;另一方面,健全财政体制,使财政更好、更健康地发挥作用,这是明代钞法带给我们的现实性启示。
参考文献
[1] 乔晓金.明代钞币初探[J].中国货币,1983(2).
[2] 唐文基.论明朝的宝钞政策[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1).
[3] 孙兵.明洪武朝宝钞的印造与支出探微[J].江西社会科学,2003(8).
[4] 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三联书店,2015:60.
[6] 王纪潮.论明代钞法的废弛[M]//中国钱币论文集.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
[7] 王玉祥.明朝钞法论述[J].甘肃社会科学,1997(5).
[8] 陈昆,李志斌.财政压力、货币超发与明代宝钞制度[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7).
[9] 张彬村.明朝纸币崩溃的原因[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3).
[10] 陈昆,李志斌.财政压力、货币超发与明代宝钞制度[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7).
[11] 唐文基.论明朝的宝钞政策[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1).
[12]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858,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
[13]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858,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
[14]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85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伍佰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15]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85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二十二年诏: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
[16]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85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
[17]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85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
[18]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85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钱,商稅兼收钱钞,钱三钞七。”
[19]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85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十三年:“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所在置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
[20]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四:834,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所在筑城濬陂,百役具举,迄于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
[21]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四:834,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
[22] 洪振快.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3]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六十九志第五十七:880,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光禄寺……掌祭享宴劳酒醴膳羞之事。”
[24]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八·户部二十五:479-480:“圣祖封藩,初拟亲王五万石,既以官吏军士俸给弥广,因监唐宋之制定为万石,后令米钞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于折者,其则不同。今天潢日蕃而民赋有限,势不能供,且冒滥滋多,奸弊百出。故嘉靖间更定条例,万历十年复颁要例宗祿皆有限制详列于后。祿米额数:亲王米一万石、郡王米二千石、镇国将军米一千石、辅国将军米八百石、奉国将军米六百石、镇国中尉米四百石、辅国中尉米三百石、奉国中尉米二百石、公主及驸马米二千石、郡主及仪宾米八百石、县主及仪宾米六百石、郡君及仪宾米四百石、县君及仪宾米三百石、乡君及仪宾米二百石。”
[25]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四十一·户部二十八:530:“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内外大军关支月盐,有家小者月支二斤,无家小者月支一斤……其在外卫所军士,月盐亦有支钞,去处每盐一斤,折钞一百文,照例行移有司于官钱内支给,如有事故一体扣除。”
[26] (明)陈子龙,辑.皇明经世文编:1687,明崇祯平露堂刻本:“灶丁办盐,毎引四百斤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
[27] (清)嵇璜,撰.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18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英宗正统元年三月少保黄福请出银收钞”:“福言,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钞法之坏莫甚於此,宜量出官银,差人于两京各省人烟辏集处,照彼时直,倒换旧钞,年终解京。俟旧钞既少,然后量出新钞,换银解京。奏下,户部不行。”
[28] (清)嵇璜,撰.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権考:390,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成祖永乐二年八月行户口食盐纳钞法”:“食盐纳钞始于洪武三年,令民于河南开封等处输米以佐军食,官给盐偿之,毎户大口月一斤,小口半之……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因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食盐之法,通计天下人民,不下千万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计口收钞,钞必可重。乃命定大小口岁食盐斤,如元年所定,毎斤纳钞一贯。”
[29] (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1877,明崇祯平露堂刻本:“若门摊一节,则祖宗已有成法,至今行之……祖宗之法,止稅店面。”
[30]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89,明万历内府刻本:“四年,令顺天、应天、苏松、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眞,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福建福州、建寧,湖广武昌、荆州,江西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东广州,河南开封,山东济南、济寧、徳州、临清,广西桂林,山西太原、平阳、蒲州,四川成都、重庆、瀘州共三十三府州县市镇店肆门攤税课加五倍,候钞法通止。”
[31]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89,明万历内府刻本:“又令榜谕两京军民官员人等,菜园果园及塌房车房店舍,停塌客商物货者,不分给公自置,凡菜地每亩月纪旧钞三百贯,果树每十株歲纳钞一百贯,房舍每间月纳钞五百贯。差御史同户部官各一员,按月催收送库。如有隐瞒不报及不纳钞者,地亩树株房舍没官,犯人治罪。其园地自种食用,非发卖取利者不在纳钞之例。”
[32]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89,明万历内府刻本:“又令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都司并直隶卫所军职官及各处镇守内外官家,下开垦由上,每亩岁纳旧钞三十贯,菜地毎亩、果树每十株岁纳旧钞五十贯,候钞法通止。”
[33]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90,明万历内府刻本:“六年,令各处地亩菜园,钞皆減半,每亩止纳钞一百五十贯。”
[34]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89,明万历内府刻本:“又令榜谕两京军民官员人等……停塌客商物货者,不分给公自置……房舍每间月纳钞五百贯。”
[35]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89,明万历内府刻本:“又令油房、磨房毎座逐月连纳门摊钞五百贯,堆卖木植烧造砖瓦,逐月连纳门摊钞四百贯。”
[36]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90,明万历内府刻本:“令各处,见收税课及船车门摊地亩果木等项,一应钞,除正额但为钞法加增之数,以十分为率減四分。”
[37]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89,明万历内府刻本:“四年,令塌房及车辆钞皆減半征收,其自己房屋与人寄筐柜者免纳钞。”
[38]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89,明万历内府刻本:“又令民间行使驴羸车装载物货者,每辆纳钞二百贯,牛车五十贯。”
[39]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89,明万历内府刻本:“牛车受雇装载货物者,纳钞五十贯,小车十贯。”
[40]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八:389,明万历内府刻本:“又令受雇装载船,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寧,济寧至临清,临清至通州俱每百料纳钞一百贯;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者,每百料纳钞五百贯。若止载柴草粮米及空船回还者,不在纳钞之例。”
[41] (明)赵用贤,撰.大明会典·卷一百七十六·刑部十八:1663,明万历内府刻本:“宣徳二年,定笞杖罪囚,每一十赎钞二十贯;其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並折杖一百四十,其所罰钞悉如笞杖所定。”
(1) (明)徐学聚,撰.国朝典汇·卷九十四·户部八·钞法[M].明天启四年徐兴参刻本:1289.
(2) (清)夏燮,编.明通鉴·卷一[M].清同治刻本:91.
(3) (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835.
(4)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四[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834.
(5) (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七[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859.
(6) (清)傅维麟.明书·卷八十一志二十[M].清畿辅丛书本:813.
(7)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四·户部[M].明天启四年徐兴参刻本:1290.
(8) 可以计算得通货膨胀税为 。但由于式子过于复杂且没有使用的必要,以An代替即可。
。但由于式子过于复杂且没有使用的必要,以An代替即可。
证明如下:
第n期初,流通中的宝钞的总量为 。
。
前n-1期的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宝钞实际总购买力下降为 。
。
所以第n期的实际贬值效果 为
为

整理可得

时期末的货币总量为 ,而时期初的货币总量为
,而时期初的货币总量为 。
。
因此,第n期的通货膨胀税Tn等于

将公式(1a)代入公式(2)即可得到待证明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