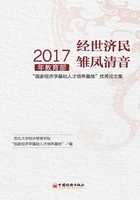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基于2011—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李晴川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污染治理成本,挤占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波特假说”认为长期内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会刺激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弥补因规制额外增加的成本费用,产生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有助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不仅会通过“挤出效应”“补偿效应”等直接途径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还会通过FDI、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创新研发投入等间接渠道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影响。本文利用2011—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创新性地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两个角度剖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并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双重效应;空间异质性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在解决污染难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及扩散。而技术创新在促进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必须将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由于环境问题自身所拥有的负外部性及“公共产品”的性质,难以界定其产权归属,从而致使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环境问题,导致“市场失灵”,为弥补此缺陷,政府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显得尤为必要。我国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间的权衡,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会推动企业成本提高、阻碍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是否会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甚至拖累经济发展,成为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生产成本、挤占R&D资金,从而给产业绩效带来直接影响,但“波特假说”却支持政府实施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认为它能够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从而产生创新补偿作用,不仅可以使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得到弥补,甚至还带来了额外的收益。对于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两者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主要观点大致可总结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肯定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支持“波特假说”。Lanjouw和Mody通过考察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的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技术传播之间的联系,得出加强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力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这一结论(1);Wilcoxen,Zeeuw和Xepapadeas等提出创新在合理情境下存在减少甚至完全弥补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的可能(2)。Cohen和Brunner Meier通过实证方法分析了美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治污成本与环境专利数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3)。现今国内以黄平(4)、刘志彪(5)、沈能、刘凤朝(6)和张成(7)等为代表的学者普遍支持“波特假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阻碍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反对“波特假说”。Gray通过研究1958—1980年美国450个制造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给生产率的增长率带来年均0.57%的下降(8);Barbera和McConnell通过考察美国化工、钢铁、金属与非金属制品以及造纸业等行业,发现其绩效下降主要归因于环境规制提高了污染治理投资(9)。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Lanoie,Patry和Lajeunesse通过对1985—1994年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制造业数据的研究,得出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长期影响为正、短期影响为负的结论,认为这种影响存在时期差异(10)。Boyd和McClelland通过考察1988—1992年美国的纸浆和造纸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不仅存在使潜在产出发生损失的情况,也存在使产出增加的情况(11)。演化经济学认为,并非所有环境规制都存在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作用,同时,并非所有技术创新都受益于环境规制,这是因为企业异质性的存在使其无法遵循同一个行为准则。目前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的关系还没有统一的结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们已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然而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多要素互动的过程,不仅会受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还会受到研发的基础设施、创新投入、制度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作用。当处于环境规制约束下时,这些要素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会改变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甚至方向。因此,除了研究环境规制如何直接影响技术创新,它的间接影响效应也值得探讨。以上文献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问题研究的文献还较少,并且多以全国为单位,忽视了环境规制给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效应在空间上的异质性。
因此,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研究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影响的机理的时候,采取了直接影响效应与间接影响效应两条分析路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并将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见表1),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表1 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

三、现状分析
本部分主要对中国科技创新情况、环境污染与治理3个方面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科技创新现状分析
近十年来,我国在科学研究上的投入逐年攀升,并且具有极大的增长幅度。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上的经费支出从2006年的3003.1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4169.88亿元,增长了近3倍。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则从2006年的150.25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375.88万人,增幅极大。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得以深入实施,整个社会创新的激情与活力被充分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
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可以用专利的申请受理量以及授权量来衡量。在我国,专利被划分为发明、实用新颖与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指对生产的产品以及生产的方法,或者对其流程与方法的改进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技术型方案;而实用新型专利是指那些对产品的形状、结构或者是结合方式所提出的一种更为实用的新式技术型方案;另外,外观设计专利是指针对产品的外形、图案的色彩或者其结合的整体所做出的一种富有美感并适合在工业实际应用中采用的新型设计。相对于发明专利来说,后两种专利所含的技术元素比较少,比较容易被学习模仿。因而可知,一个地区的发明专利的申请受理以及授权量是最能体现其技术创新水平的。
我国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专利申请受理量从2006年的470342项增长到2015年的2639446项,增长了4.61倍,专利申请授权量则由2006年的223860项增长到1596977项。然而在2012—2014年,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呈现出停滞现象。从不同专利种类申请受理量看,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逐年攀升,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与全国变化趋势相似,总体上升,但在2012—2014年趋于停滞。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受理量所占比重大体相似,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受理量从2013年开始占比逐渐减小。而从不同专利种类申请授权量来看,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极小。

图1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人员全时当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图2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图3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图4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分区域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专利授权数量表示这种创新成果通过了国家认证,发挥了作用。从我国专利授权量变化趋势来看,2006—2015年总体呈上升趋势,由208761项增长到1578241项,但在2012—2014年出现停滞。东部专利授权量较大,与全国变化趋势相似,中部和西部专利授权量较少,虽呈现上升态势但幅度不大,且中西部授权数量极为接近。这说明中国技术创新水平虽呈上升趋势,但全国的技术创新主要是东部地区贡献的,中西部技术创新远赶不上东部,区域差异明显,两极分化严重。
(二)中国环境污染与治理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踏入社会主义工业化阶段,工业渐渐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的难题。由图5可以看出,2000—2015年中国工业废气排放量上升趋势明显,由2000年的13814.5立方千米上升至2015年的68519立方千米,但在2011年后趋于平缓,可能是规制抑制了废气排放量的上升。从图5中可以看出,SO2排放量占废气排放总量的绝大部分,环境规制对SO2排放量的减少并未起到很好的效果。工业废水的排放总量趋势平稳,但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3186.2万吨下降到2015年的55.8万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环境规制有效遏制了固体废弃物的排放。但从污染的总体情况来说,污染物的排放量是上升的。

图5 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从图6中可以看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11年的7114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8806.4亿元,5年间峰值出现在2014年,总投资9575.5亿元,2014—2015年略有下降。东、中、西三大区域变化趋势与全国大体一致,从分布来看,东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远大于中部和西部。从图7中可以看出,中国环境治理设施当年运行费用除2011—2012年略有减少外,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11年的2311.627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3318.2763亿元,东、中、西三大区域变化趋势与全国大体一致,从分布来看,环境治理设施当年运行费用远大于中部和西部。总体来看,环境规制的强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东部的环境规制强度远大于中部和西部。

图6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数据来源:2011—2016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图7 治理设施本年运行费用
数据来源:2011—2016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四、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随着世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开始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环境规制不仅会通过“挤出效应”“补偿效应”等途径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还会通过FDI、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创新研发投入等渠道间接影响技术创新。该部分将对这些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它们的作用机理作逐一分析。
(一)直接影响效应
政府环境规制会给企业生产带来额外的约束条件,这可能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挤出研发资金从而直接阻碍技术创新,也可能诱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保持利润不变或增加,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因此,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既可能存在“挤出效应”,也可能会有“补偿效应”。
1. 挤出效应
环境规制会从两个主要方面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一是挤出创新研发资金。在政府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需要将有限资金投入污染治理过程,或者被迫引进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生产设备、生产方法。而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用于治污减排的投资便会挤占原本用于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污染治理成本的提高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二是挤出投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企业面临环境保护带来的沉重压力,运行和投资成本大大增加,致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渐渐丧失原有竞争力。这些企业往往会倾向于将污染产业转移,在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地区重新布置生产和投资,减少在当地的创新投入和投资份额。这也是导致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天堂”的原因。
通过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施行赋予了环境资源以经济物品的性质(12),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时不得不为其消耗的环境资源支付一定的费用,由此增加的生产成本会推动产品价格上升,在市场需求条件保持不变时,企业利润率会相应下降,抑制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另外,当企业服从严格的环境规制时,还会额外支出一些人力资源,占用相当比例的管理时间。
2. 补偿效应
首先,环境规制通过对生产所占用的社会资源限定范围或者收取费用,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作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在面临这种要素价格变化和生产成本增加时,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若不进行创新就难以生存。因此,环境规制赋予了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迫使其将注意力集中于环境保护与提高产品质量上,用于改良生产工艺以及提高治污水平的技术创新,能够减少环境规制给企业造成的额外成本,甚至可以完全抵销,这便产生了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
其次,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设置进入壁垒,从而创造出超越平均水平的“经济租金”(13),因此,环境规制会给予企业先动优势激励。若有企业率先创造出满足政府环境规制要求的技术创新成果,可为其申请专利获得保护,环境规制会约束社会上所有企业,其他企业若想采用其技术从事生产活动,必须向拥有专利的企业支付费用。这种潜在创新收益将会激励企业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最后,在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实施的同时,政府常会在产业以及财政政策上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这将会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创新资金不足的问题。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还能提高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并且使个人和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解决。社会公众的监督能够促进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由以上分析可知,环境规制给技术创新造成的直接影响效应具有两面性。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会根据服从规制的成本与技术创新成本的相对大小来选择是否进行技术创新,“波特假说”成立与否取决于两方面的相互权衡。服从环境规制的成本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而增加,当服从规制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的的企业往往会选择进行技术创新。
(二)间接影响效应
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存在直接影响效应,还可能会通过影响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与企业的规模效应、人力资本的技术创新效应与企业的创新研发资金投入等间接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
1. 外商直接投资(FDI)
环境规制会通过影响FDI投资区位的选择、内资企业FDI吸收能力以及政府引资政策等,使FDI的技术创新效应受到影响。开放经济条件下,FDI可以通过竞争、示范与模仿效应,前后向关联效应等渠道在产业内发挥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从而影响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从环境规制改变FDI投资的区位选择的角度来说,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在面临严格环境规制所带来的高昂生产成本时,会将其污染密集型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地区(14)。另外,严格的环境规制会给外资设置相对较高的“环境门槛”,阻碍其进入(15)。因此,“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会对产业区位选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16)。
从环境规制影响内资企业FDI吸收能力的角度来说,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将会挤占资金有限的企业原本用于培训和研发的资金,从而导致本土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降低,难以得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好处。
从环境规制影响政府引资政策的角度来说,政府加强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力度时,会调整外资引进政策,有选择地引进外资,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比如,在减少引进污染密集型外资企业的同时,给引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更多支持。积极引进优质FDI,有利于其与国内企业进行有效竞争,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因而环境规制通过改变FDI质量能够给企业技术创新带来正向促进作用。
2. 企业规模
一方面,由于大多数技术创新需要高昂的成本并且需要承担极大风险,这意味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只有具有相当规模且拥有丰富资源的企业才能够胜任。阈值理论强调在创新上,大规模的和垄断的企业具有较大优势,因为它们往往拥有充足的资金,且风险承受能力较强(17)。
然而另一方面,大企业具有的资金优势和规模优势若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则可能会被遏制,进而会影响到其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首先,大规模企业有着比小规模企业更高的投入与产出,因而它们为达到环境规制的要求,往往需要比小规模企业投入更大的环保支出,因此弱化了其原本优于小规模企业的资金以及规模优势。其次,大企业往往掌握着更多物质上、政治上的资源,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相较于中小型民营企业而言。当大企业“暴露”在严格环境规制的环境中时,更倾向于向政府“寻租”,由此带来资源、资金的无效利用,这将极大地降低企业的创新水平。
3. 人力资本水平
企业的资金预算有限,在面临环境规制带来的额外生产成本时,会选择减少用于培训的费用以及付给员工的工资,从而限制了人力资本发挥其技术创新效应。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需要积累充足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会随着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加快。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吸收和转化能力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但是,在有限的预算范围内,环境规制可能会逼迫企业采取压缩劳动成本、降低培训费用、调整生产投资等措施弥补额外的成本,从而阻碍企业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以维持企业的利润水平。这会导致企业技术吸收和创新能力的降低。
4. 创新研发资金投入
作为一种新知识的“生产”过程,技术创新离不开科技人员、机器设备以及研发经费等资源的投入,其中资金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但是,企业往往拥有有限的资金预算,当其面临严格的环境规制时,用于治污环节的费用会挤占原有的研发资金,从而会降低其技术创新的能力。可是当企业拥有的创新研发资金越充足,其中被治污成本挤占的那部分在庞大的资金数额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小,因此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受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会随着创新研发资金投入的增加而逐渐减小。通常情况下,即使面临政府的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仍然与创新研发资金的投入数量呈正向关系。
综上所述,政府的环境规制一方面会通过“挤出效应”或“补偿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规模、人力资本水平、创新研发资金投入等多种间接渠道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现提出3个假说:
假说1: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具有差异,较强时会给技术创新带来“补偿效应”,而较弱的环境规制则会产生“挤出效应”。
假说2:FDI、企业规模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与它们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对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假说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存在空间异质性。
五、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分别探索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生的直接效应影响,以及环境规制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对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影响,本文分别构建了两个包括截面数据(31个省份)和时序数据(2011—2015年5年间)的面板数据模型。并且,在考察其直接影响时将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探索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直接影响的空间差异。该面板数据模型样本容量巨大,可以有效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为消除变量的量纲,并且避免异方差及异常项对数据的平稳性影响,所有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模型1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模型,模型2为环境规制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对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效应模型,其中,用i地区t期的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技术创新能力,表示为Patentit;i地区第t期的环境规制由ersit表示。模型1中,控制变量由fdiit(FDI),sizeit(企业平均规模),rlzbit(人力资本),rdzit(创新经费投入)等变量构成。同时,模型2构建了环境规制的间接影响效应模型,其中Efdit,Esiit,Erlit,Erdit分别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一(Ers1)与fdi、企业平均规模、人力资本、创新经费投入等变量的交互项,Efd2it,Esi2it,Erl2it,Erd2it分别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二(Ers2)与fdi、企业平均规模、人力资本、创新经费投入等变量的交互项,i表示第i个省份,t表示t时期。C表示不随个体变化的截距,β表示待估参数,Vi表示个体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由2011—2015年全国各省的数据整理和计算而得。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地方统计年鉴、国家以及各地方统计局数据库、《中国环境年鉴》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1. 技术创新(patent)
在现有文献对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之中,学者们广泛采用专利数量这一指标衡量技术创新产出。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已有研究,本文采用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技术创新产出。一是因为专利授权数量能够侧面衡量技术创新的能力以及水平,二是仅有专利授权数量表示这种创新成果通过了国家认证,发挥了作用。
2. 环境规制强度(ers)
由于获取环境规制强度相关数据存在一定难度,且其数据质量难以保证,限制了环境规制问题的研究,学界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标准存在较大争议。现今,在度量环境规制强度的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用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数量来代表环境规制强度的高低;二是采取治理污染总投资占工业总产值或企业总成本的比重来衡量;三是采用治理污染设施运行费用衡量;四是研究内生环境规制强度时采用人均收入水平作为代理变量;五是根据不同污染物的排放密度来衡量;六是在环境规制的条件下用某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情况来度量。上述6种对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基于数据可得性与保留指标的相对完善性的考虑,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内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以及各省份环境保护支出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前者为指标一(ers1),后者为指标二(ers2)。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为治理废水与废气的运行费用之和,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环境年鉴》。
3. 外商直接投资(fdi)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一国研发创新活动越来越依赖全球的共同努力,FDI的地位不言自明。国家可以通过共享全球的知识、技术、资金以及人力资源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本文选取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其中用GDP平减指数平减GDP(以2010年作为基期),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4. 企业平均规模(size)
“熊彼特假说”认为,相对于规模较大企业而言,小规模企业的创新动机不强,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并不占优势。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其资源的跨地区整合与利用,尤其是创新资源的分享,从而为其带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规模大的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生产率相对越高。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大规模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更强,因为它们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来进行技术创新。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原则,本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合计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来表示企业平均规模。
5. 人力资本水平(rlzb)
科技活动人员的劳动力是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主力军,要想提高研发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各地区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会给技术创新带来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用以衡量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操作方法为将6岁及以上的人口作为总样本,并假设各级别教育的年限分别是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以上的教育程度则为16年。
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
6. 创新经费投入(rdz)
创新经费投入为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对于该变量,本文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衡量,并将基期定为2010年,对R&D经费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去进行平减。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六、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 8.0,在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对以上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并由F统计量与Hausman统计量确定模型形式。前者用以检验是否应建立混合模型(经检验所有模型均不为混合模型),后者用以检验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最后利用OLS法估计回归参数。
(一)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虚假回归的存在,在回归前对面板数据模型中所有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为避免单一检验方法可能存在的缺陷,本文将采用Levin-Lin-Chu(LLC),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Phillips-Perron(PP)3种面板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当大多数检验拒绝变量不平稳的原假设时则认为变量平稳。由检验结果(见表3)可知所有变量均具有平稳性。
表3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续表

(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分析
根据上文构建的模型1,分别建立全国全部31个省份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影响的模型1-1,再将31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建立模型1-2、模型1-3、模型1-4,分别探索不同空间范围内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
表4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

续表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据为t统计量。
(1)模型1-1的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正相关,影响系数为0.177906,在5%的水平下显著。每增加1单位环境规制强度(ers1),会给技术创新带来17.8%的增长。企业是否选择进行技术创新,取决于服从规制与技术创新两者间成本的相对大小。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意味着服从环境规制的成本也较低,此时企业的创新动力不够。服从环境规制的成本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而增加,当服从规制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的的企业往往会选择进行技术创新。模型1-1表明对全国而言,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可能会造成污染治理成本占企业总成本较大份额,因而形成对企业的“倒逼机制”,使其不得不增加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治污技术水平并改进生产工艺,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因此,产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并且使企业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在满足政府环境规制的要求的同时得以维持利润率不变。
模型1-2显示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则为0.126506,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不过小于模型1-1中全国的影响系数,说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带来的“补偿效应”小于全国。模型1-3则显示在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变为-0.053752,呈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而模型1-4显示的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为-0.34894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两者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比较弱的中西部地区也被削弱了。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相对东部甚至全国而言偏弱,污染治理成本较低,这会使企业在治污减排和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动力不足,增加的治污成本反而可能挤占了企业原有的研发资金,产生“挤出效应”。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随着规制程度的加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会逐渐由“挤出”变成“补偿”。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验证了假说一。
(2)模型1-1显示以全国作为考虑范围的FDI系数显著为正,影响系数为0.190396,表明开放经济条件下,FDI可以通过竞争、示范与模仿效应、前后向关联效应等渠道在产业内发挥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型1-2、模型1-3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FDI系数显著为正,影响系数分别为0.581823、0.33505,表明这些地区外资的引进有利于该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时,东部地区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由于其沿海的独特地理优势,使得外向型经济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外资大量涌入的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大大推动了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促进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而模型1-4显示西部地区FDI系数并不显著,由于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发展起步晚,外资引进的程度远远不及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还并不明显。
(3)模型1-1的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面影响,影响系数为0.918732,在1%的水平下显著,企业规模每1单位的扩张会促进技术创新提升91.8%,说明在技术创新上,大企业的研发投入比小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效应,验证了Joseph Alois Schumpeter对于企业规模与创新的观点。大企业具有更为雄厚的资金保障,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并且在过程创新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模型1-2、模型1-3的结果都显示以东部和中部地区为单位的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正面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97738、0.639102,在5%、5%的水平下显著。而模型1-4显示西部地区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影响系数为-1.071455,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企业规模盲目扩张给其带来了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无法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4)全国范围内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贡献率极大,影响系数达到2.49951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需要积累充足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会随着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加快;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吸收和转化能力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5)以上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研发资金投入每上升1个单位,专利授权量约增加0.65个单位,研发资金投入对东、中、西三大区域技术创新都呈正面影响,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这也证明研发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和西部地区研发资金会给技术创新带来比东部地区更大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技术创新受到研发资金的限制程度较小。
(6)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规制程度上,东部地区高于中部,而西部最低,重视环保的东部地区必然重视人才以及相关技术领域的创新,政府也会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激励企业研发新的环保技术。同时,中国东部区域具有比中西部地区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产业密集,竞争激烈,这也激励着东部地区的企业不断进行创新。此外,东部凭借其远超于中西部地区的良好政策福利待遇以及适于发展人才的环境,不断吸引着许多高质量人才,从而提高了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给技术创新提供了充分的人力资本保障。因此,东部地区拥有一系列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的优越条件。而中部区域虽然在中部崛起和建设两型社会的政策倾斜下,环境规制逐渐严格,但仍受硬件条件的制约,还处于起步阶段,对技术创新还不足以造成显著的影响。对创新起重要作用的要素,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资本投入等在西部地区都较为薄弱,由此可知西部地区不仅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不足,自身创新能力也不够,因此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很难发挥。
(三)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分析
根据上文建立的模型2,依次加入Esi,Erl,Efd,Erd等环境规制与企业平均规模、人力资本、FDI、创新经费投入等交互项,建立模型2-1、模型2-2、模型2-3,考察环境规制通过间接渠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表5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据为t统计量。
通过对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创新经费投入等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FDI、企业规模、创新经费投入等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符号并未发生变化,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却由正变为负。并且随着模型中变量的增加,每个解释变量给专利授权量增长带来的贡献率也在减小,表现为影响系数的绝对值随着解释变量的增加而减少。这说明随着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的增加,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单个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逐渐减小,影响因素的复杂化也使得环境规制约束下,无论FDI、企业规模、人力资本还是创新经费投入都不会对促进或制约技术创新起决定作用。
在存在环境规制的情况下FDI的影响系数依旧为正,证明了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技术创新无任何不利的影响,甚至还具有正向的刺激促进作用。这是因为积极引进优质FDI,有利于其与国内企业进行有效竞争,进而促进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从环境规制影响政府引资政策的角度来说,政府加强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力度时,为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会在减少引进污染密集型外资企业的同时,给引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更多的支持,引进的这些企业往往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给技术创新带来积极的正面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规模交互项符号依旧为正,说明在我国的环境规制约束下,大企业的规模优势以及其在研发投入方面存在的资金优势并未受到抑制,也并未对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然而,环境规制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却由正变为负,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环境规制约束下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是负面的。虽然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动力和源泉,它的获取、吸收和转化能力直接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往往采取压缩劳动成本、降低培训费用以及调整生产投资等措施对有限的资金预算作出反应,弥补因环境规制提高的治污成本,从而阻碍了企业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这会导致企业技术吸收和创新能力的降低。
(四)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检验结果的稳定性,进一步对上述模型1-1、模型1-2、模型1-3、模型1-4以及模型2-1、模型2-2、模型2-3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将31个省份环境保护支出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当作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指标ers2。环境规制的强度越高,该变量的数值越大。本文重新对上文构建的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见表6)。结果表明,7个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以及符号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可以认为以上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是稳健的;而模型1-3、模型1-4中第一个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上文回归结果有差异,即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专利授权量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与上文有差异,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对有关环境研发的数据进行专门统计,用特定的测算方法所得到的数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误差;二是由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表现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指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应具有异质性,这同样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续表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据为t统计量。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企业在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受到了“知识产权瓶颈”和“资源瓶颈”的双重约束,本文运用2011—2015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将其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分别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的双重影响效应及其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①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给技术创新带来的直接影响效应不同,环境规制较强时,会对技术创新产生“补偿效应”,而较弱时则会产生“挤出效应”;②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强度由东部至中部再到西部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生“补偿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则会产生“挤出效应”;③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企业规模以及研发经费投入等仍然会对技术创新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然而环境规制却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技术创新效应,企业会选择压缩劳动成本、降低培训费用以及调整生产投资预算等方式来弥补由环境规制带来的额外治污成本,从而影响了人力资本的技术创新效应,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
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好的政策参考价值,即在促进环境保护的同时兼顾技术的创新与升级,本文提出以下4点政策建议:
(一)制定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
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会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应综合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以及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状况、产业结构的实际,制定并实施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一般情况下,具有较强强制性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缺乏对企业的足够激励,如环境标准、排放限额等“控制型”工具;而“激励型”政策工具却能持续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常见的此类环境政策工具有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等(18)。对于污染严重的地区及污染密集的产业,需要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强度,政府应实施“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而对于污染相对较轻的地区以及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可采取“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企业提高治污水平并推动其生产技术的创新,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二)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力度
开展技术创新需要充分的资金保障。由于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用于技术创新资金的充分使用以及大企业规模效应的发挥具有不利影响,政府应对企业技术研发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例如,设立专项资金、提高财政补贴,为大企业开拓更广泛的融资渠道,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现规制措施的差异化与灵活化,为促进其技术升级提供制度保障。另外,中国目前的科研管理体制也可以进行适当调整,即政府仍着重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但是应用科学研究应转变为主要由企业承担。政府预先公布某项待研发的技术,寻求全体相关企业参与研发,随后择优购买企业的研究成果。从而既可以避免现有体制下政府事前盲目发放科研经费而造成的资金使用低效率现象,还能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推动其成为创新主体,从而为经济长期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三)制定合理的招商引资政策
我国始终坚持开放政策,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但与此同时,还要转变过去因短期利益为外资企业提供“超国民待遇”政策优惠的观念,这是为实现短期经济利益而牺牲环境的观念。所以,政府必须转变引进外资的思路,综合考虑本地区实际,引进优质FDI以及适宜的技术经验,并在“引资”的同时做到“引技”,通过引进高质量外资企业与前沿技术来促进本地技术水平的提升。另外,还应重视外资企业和当地主导产业两者间的配套,并帮助提升内资企业的吸纳力和二次创新能力,促进其转型升级与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在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是企业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作用于技术创新活动:一是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提升知识与技术储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二是积累人力资本而提升对来自海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吸纳能力。人力资本可以对技术创新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环境规制制约了这一机制的正常发挥。因此,为抵消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效应,政府应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教育投资总体增长的同时,国家还需相应地调整投资结构,相对加大其对中西部地区及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从而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在区域间的平衡。此外,政府与企业需建立有效的机制,为人才引进工作提供资金、平台等方面的政策扶持,通过“引智”提升本地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 Lanjouw J. O., Mody A. Innov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ve Technology[J]. Research Policy, 1996, 25(4): 549-571.
[2] Wilcoxen, P.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R]. Mimeo,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8.
[3] Brunner, M. S. B., Cohen, M. A.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45(2): 278-293.
[4] Gray, W. B. The Cost of Regulation: OSHA, EPA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77(5): 998-1006.
[5] Barbera, A. J., Mc Connel, V. 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Industry Productivity: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0, 18(1): 50-65.
[6] Lanoie, P., Patry, M., Lajeunesse, 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New Finding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R]. Working Paper, 2001.
[7] Boyd, G. A., Mc Clelland, J. 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on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Integrated Paper Plan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sand Management, 1999, 38(2): 121-142.
[8] Bailey, J. A. Brush Control on Sandy Rangelands in Central Alberta[J]. Journal of Range Management, 1974(32): 65-68.
[9] Ambec, S., Cohen, M., Elgie, S., et al. The Porter Hypothesis at 20: C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hanc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J].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Discussion Paper, 2011: 1-11.
[10] Baumol William, J., Wallace, E. Oates.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 Ederington, J.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Trade and Domestic Polic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5): 1580-1593.
[12] Levinson, A.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Manufacturers' Location Choices: Evidence from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 62(1): 5-29.
[13] 黄平,胡日东.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相互促进的机理与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1):99-103.
[14] 黄德春,刘志彪.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J].中国工业经济,2006(3):100-106.
[15] 沈能,刘凤朝.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2(4):49-59.
[16] 张成,陆旸,郭路,等.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123.
[17]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易家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8] 李玲,陶锋.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5):70-82.
(1) Lanjouw, J. O., Mody, A. Innov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ve Technology[J]. Research Policy, 1996, 25(4): 549-571.
(2) Wilcoxen, P.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R]. Mimeo,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8.
(3) Brunner, M. S. B. Cohen M. A.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45(2): 278-293.
(4) 黄平,胡日东.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相互促进的机理与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1):99-103.
(5) 黄德春,刘志彪.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J].中国工业经济,2006(3):100-106.
(6) 沈能,刘凤朝.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2(4):49-59.
(7) 张成,陆旸,郭路,等.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123.
(8) Gray W. B. The Cost of Regulation: OSHA, EPA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77(5): 998-1006.
(9) Barbera, A. J., Mc Connel V. 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Industry Productivity: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0, 18(1): 50-65.
(10) Lanoie, P., Patry, M., Lajeunesse 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New Finding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R]. Working Paper, 2001.
(11) Boyd, G. A., Mc Clelland, J 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on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Integrated Paper Plan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sand Management, 1999, 38(2): 121-142.
(12) Bailey, J. A. Brush Control on Sandy Rangelands in Central Alberta[J]. Journal of Range Management, 1974, 32: 65-68.
(13) Ambec, S., Cohen, M., Elgie, S., et al. The Porter Hypothesis at 20: C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hanc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J].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Discussion Paper, 2011: 1-11.
(14) Baumol William, J., Wallace, E. Oates.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 Ederington J.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Trade and Domestic Polic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5): 1580-1593.
(16) Levinson, A.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Manufacturers' Location Choices: Evidence from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 62(1): 5-29.
(17)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易家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8) 李玲,陶锋.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5):7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