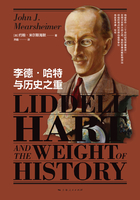
第一章
引言:重新评估的必要
巴兹尔·亨利·李德·哈特爵士1970年去世时,他是世界上最为著名并且广受尊敬的军事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并且在今天仍然如此。学者、政治家和军官们对他大加赞赏,牛津大学已故教授、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阿拉斯泰尔·巴肯(Alastair Buchan)称他是“机械化时代最为重要的军事思想家,并且明确地预见到内燃机和飞机对战争的影响”;英国的军事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称他是“本世纪(20世纪)最伟大的战争思想家”;A. J. P.泰勒(Taylor)将他描述为“这个时代最令人敬畏的军事作家”。美国历史学家杰伊·卢瓦斯(Jay Luvaas)称他是“现代史上知识最渊博、最具创造性和最有影响力的军事思想家之一”;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成为总统之前写道:“没有其他的军事问题专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他罕有地将专业知识和充满想象力的洞见结合在一起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他的预测和警告经常是正确的。”1
一些著名的德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指挥官也给予他类似的称赞,并且将他们在战场上的成就归功于他。20世纪30年代德国装甲力量的推动者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强大部队的指挥官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称自己是“在坦克战术上李德·哈特的信徒”。另一位德国装甲部队的将军,哈索·冯·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称李德·哈特为“现代坦克战略的创始人”。以色列军队的塑造者之一,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称他是“将军们的上尉老师”;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在他的一张照片上题写“我们所有人最伟大的老师”。2
巴兹尔·哈特1895年10月31日出生在巴黎。他的父亲来自一个名为康沃尔郡的家族,这个家族的一部分在循道卫理运动(Methodist movement)开始时离开英格兰教会。他曾经选择在卫理会任神职,后来在法国的一个使用英国国教礼仪的卫斯理教会布道。在巴兹尔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转到巴黎另一个类似的、为众多新教徒服务的教会工作。在世纪之交后不久,他的家族又回到英格兰,在那里,他过着一个典型的爱德华时代中上阶层的生活,他去公立学校(圣保罗学校,他的家族与卫斯理和圣公会关系密切)接受教育,在那里他是一个好学生,但不是十分出色。他的早期兴趣包括军事战术、历史、体育和航空。在他快过19岁生日并且即将开始在剑桥大学读历史专业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满腔热情地参军,在1914年12月成为皇家约克郡轻步兵的一名中尉。他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剑桥完成他的学业。3
在1915年秋季,他被派遣到法国参加战斗。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三次在前线参加战斗。他在战区的前两次经历相对平常,但是最后一次他参加了著名的1916年索姆河战役,在这场战役的第一天,英国军队就有6000人伤亡。在战役的第三周,他中毒严重并被送回英国,在那里他主要负责为西线训练步兵。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开始进行军事问题写作,开启了他引人注目的持续50年的写作生涯。直到1924年他才离开军队,由于心脏有问题他被迫退役。4在那之后不久,他成了《每日电讯报》的军事记者,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935年,直到转到更著名的《泰晤士报》工作。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除了报纸专栏之外,他还撰写了很多书和杂志文章,包括有关步兵战术、装甲战略和大战略方面一些重要的、具有创新性的作品。5
李德·哈特的作品使其很快声名远播,他成为英国在战争期间最为著名和令人尊敬的军事评论家。与伍德罗·威尔逊关系紧密的私人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M. House)上校在1933年称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军事评论家”。同一年早些时候,著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Ian Hamilton)将他称为“我们时代最有远见并且激发思考的军事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将他视为“关于现代战争的最高权威,并且能见到他是一种荣幸”。按照著名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描述:“他不仅是关于作战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理解人类冲突根源的哲学家。没有人可以如此勇敢并准确地解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20世纪30年代,他被称为自克劳塞维茨以来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或者有时被称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6
这些声誉帮助李德·哈特能够接触到政府高级官员,使他可以在英国的军事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在30年代,他没有担任任何官方职位,但他与英国关键的决策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决策者在1933年之后最为关切的就是如何对付希特勒。具体来说,英国人争论是否要建立大规模的军队帮助法国抵御德国进攻。李德·哈特坚决反对建立可以在欧洲大陆进行战斗的军队,他尽全力并且成功地使官方接受他的观点。他在《泰晤士报》的专栏,以及很多文章和专著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且与英国的高级官员进行协商,其中最著名的是莱斯利·霍尔-贝利沙(Leslie Hore-Belisha)。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1937年5月就任英国首相时,任命霍尔-贝利沙为战争大臣。哈特在这之后就成为霍尔-贝利沙的私人顾问,而贝利沙对军事事务知之甚少。因此,在1937年5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张伯伦政府在进行一些战争期间最为重要的大战略决策时,李德·哈特都能够影响政府中一位主要决策者的思维。除此之外,他还能接触到很多其他关键人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德·哈特的名声严重受损,并且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7他对战争开始几场战役的预测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德国“闪电战”的成功。他给张伯伦政府不要建立英国陆军的政策建议也被证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战争期间的英国,他一直呼吁与希特勒协商解决问题,这使他的形象进一步受损。结果是他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并且开始经历他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期。当德国侵略波兰的时候,他才43岁,以他在30年代取得的卓越成就,他本可以处于或接近战时英国的决策中心,但却只能被边缘化。在1950年之后,他的声誉又得到显著的恢复,到60年代中期,他又再次被称赞为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策顾问。他错误的预测和政策建议已经被大部分人遗忘,相反,他被赞誉为预见到30年代灾难并发出警告的先知。
从法国沦陷到他20世纪70年代去世的三十年中,他依靠写作和讲座谋生。在这些年里,他没有在任何报纸有正式的职位,也很少为政府官员提供咨询或者担任政府中的正式职位。然而,他过去和当前关于军事问题的作品使他继续为更多的读者所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军事问题不同方面的作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细节,8法国元帅马歇尔·费迪南德·福煦(Marshal Ferdinand Foch)和威廉·谢尔曼将军(William T. Sherman)的传记,9英国装甲力量发展的全面描述,10以及一本关于德国将军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11另外,他还编辑了埃尔温·隆美尔(F.M. Erwin Rommel)的私人文件,并且还撰写了一部长篇的劳伦斯(T.E. Lawrence)传记。12他还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和影响力的军事理论家,撰写了大量关于步兵战术、装甲战略和大战略的作品。除这些外,哈特还参与了早期核威慑理论的发展。13事实上,他还是50年代大规模报复理论的主要批评者。他还写了很多关于北约战略的文章。14通过这些作品,李德·哈特一直对西方战略思想有重要影响。
这本书有四个目的。第一个目标是描述并评价李德·哈特的军事思想。在两场战争之间,他发展出五个重要的军事观念。无论在防御还是进攻方面,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创造的步兵战术理论与德国陆军在战争后期引入的著名的步兵战术十分相似。有证据表明,他的理论是从德国的经验中借鉴的。他经常被认为闪电战之父,但事实上,关于这个战略他的作品很少。我们还知道是富勒(J.F.C. Fuller)使李德·哈特相信坦克对战争产生了革命化的影响,而哈特早期关于闪电战的大部分思考来源于富勒的作品。他在1925年至1931年间发展出的著名的间接路径(indirect approach)理论常常和闪电战联系在一起,但李德·哈特的本来意图是将之作为装甲战略的替代方案,目的是在不派出陆军的情况下打败欧洲大陆的敌人。事实上,哈特最初将间接路径等同于一个杜黑式(Douhet-like)的概念,即通过对敌人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空袭迫使它投降。战争中的英国方式是哈特创造的第四个理念,事实上是间接路径的另一个变种。这一理念提倡使用英国的海军力量对大陆敌人进行封锁,迫使它们屈服。最后一个是李德·哈特对装甲战中防御优势(superiority of defense)的论证。15不为大众所知的是,他在30年代中期放弃了闪电战理论,开始持相反的观点,即使拥有大量的坦克,进攻方也不大可能在战场上获胜。
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解释哈特的观念是如何发展出来的:他的战术、战略和大战略思想形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将这场冲突视为由杰出的英国将军进行的一项崇高事业。但在30年代早期,他又变成这场战争特别是英国将军的主要批评者。他的观点发生变化,认为英国将军是一群无能之辈,这直接影响了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即如果再次面对一个具有侵略性的欧洲大陆的敌人,英国是否应该致力于建设一支庞大的陆军在欧洲大陆战斗。哈特越是蔑视英国的军事力量,就越是反对所谓的大陆承诺。他对这项承诺的思考反过来直接影响了他对战略和战术问题的看法,最后使他成为“防御在战场上总是胜过进攻”这个观点的极端支持者。布赖恩·邦德(Brian Bond)在他关于李德·哈特军事思想的卓越研究中问道:“装甲战和闪电战的杰出阐释者是如何变成防御战大师的?”16这个显著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大陆承诺的立场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他对英国将军和他们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发生变化。简言之,李德·哈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态度的不断变化对他后来的军事思想投下巨大的阴影。
第三个目标是描述并评价李德·哈特在两场大战之间的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英国没能阻止德国在欧洲大陆挑起争端。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经受了很多严重的失败。最明显的就是德国在1940年5月击败法国和英国。威慑德国以及阻止他们进攻的失败引发了针对英国政策的三类问题,更加具体的是针对李德·哈特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对策建议:就李德·哈特在那时的观点来看,他是否意识到第三帝国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关于如何威慑敌人,他给出了什么样的政策建议?他是否预见到法国的沦陷并发出警告?在多大程度上他的政策建议不同于官方政策?考虑到他的影响力,他对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否产生了影响?在英国的决策圈中,他的观点是否有说服力?或者说他的观点大多被忽视?最后,李德·哈特当时所阐述的观点产生了哪些影响?
关于李德·哈特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用,被普遍接受的一个说法在他1965年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他完全理解纳粹德国所代表的危险,他是绥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并且在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发生时呼吁对抗希特勒。另外,他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状况,当时德国国防军打败法国并将英国军队赶出欧洲大陆。他的警告被其他英国人,尤其是军队领导人所忽视,保守的英国将军拒绝听从他明智的建议。他是一个在他自己的国家没有受到尊重的先知。而德国的将军,特别是那些认同装甲战和闪电战的将军反倒遵循了他的建议,并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关于他回忆录的评论有数百篇之多,几乎压倒性地支持他的观点,鲜有人对他的说法提出挑战。泰勒在审读了第二卷之后评论说:“他的第一卷得到了震耳欲聋的称赞。他的第二卷更具启发性。现在李德·哈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17迈克尔·霍华德对第一卷的评论体现出大多数评论的要义:
如果他没有相当详细地提醒我们他的战术、战略和战争作品中卓越的先见,他是不近人情的;然而,如果他对如此灾难性地忽视他意见的人能够隐藏他的急躁,他的境界又是极高的。但是……(他)没有敌意。有坦率的批评,但从来没有怨恨。结果是,他的判断很少被证明是没有说服力的。18
这些称赞很多来自著名的学者,这说明李德·哈特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例如,当议会军事改革党团会议在1981年12月举办第一次记者会时,它的主要发言人说:
我深深感到不安,我们没有准备好以我们曾经那样的确信捍卫我们的自由……我感觉到大量同样的惰性,那是两场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和英国军事体制的祸根。他们忽视了像李德·哈特这样的先知,这位英国战略家呼吁战术和战略的重大改变。但是哈特的战略被德国人获得,使其在1940年达到了毁灭性的效果。19
但是存在另一种说法:李德·哈特几乎不是体制外的人,他在《泰晤士报》的职位以及他和霍尔-贝利沙的关系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的政策建议大部分与张伯伦政府是一致的。没有证据表明他是绥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或者他主张对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采取强硬立场。1939年3月之后,当英国的领导人快速地从绥靖政策转向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李德·哈特反对这种转变,并强烈地支持继续采取绥靖政策。关于他的装甲战思想被英国将军明确拒绝,但被德国将军采用的说法也绝非事实。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将呈何景象以及当德国和盟国军队最终交战时会发生什么的预测几乎完全是错误的。最后,他的政策建议弱化了英国威慑第三帝国的可能性,并减少了战争到来时英国打败德国国防军的机会。简单地说,他的回忆录是对历史记录的公然歪曲,被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讨论把我们带到本书的第四个目标:判断李德·哈特如何能够挽救他的声誉。他是如何转变公众对他在两场大战之间作用的看法?他是如何让如此多的军事问题研究者信服他的说法?李德·哈特在20世纪40年代没能成功,但是在50年代早期他的运气开始转变,当时很明显一些德国将军愿意与他合作,重写历史记录。然而,比起德国将军的错误背书,李德·哈特自己的作品对他(恢复声誉)的努力更加重要。从法国沦陷到他去世的30年时间中,他竭尽全力用自己的版本记录战争期间的事情,并且挑战任何提供不同说法的人,以他的回忆录出版而告终。李德·哈特的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不存在很多专门研究军事问题、可以挑战他对过去的描述的学者;他卓越的说服力;他努力结交朋友,部分地消除了年轻学者的不满,他知道这些人将最终书写他这个时代的历史。在很多年中,在英国或者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或者具有知识基础去挑战李德·哈特对20世纪30年代的阐释。在60年代,一个专注于军事问题,尤其是军事史的学者网络开始在英格兰形成,他通过帮助他们进行研究,使他们中很多人都对他有所亏欠,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使他们倾向于以更缺乏批判的方式接受他的观点和对过去的解读。在那时,李德·哈特已经在重塑历史记录方面做了很多。
有很合理的理由去考察李德·哈特的军事思想。他的理论继续吸引军事问题研究者。尽管他在1970年去世,并且他的主要观点在几十年前就被阐述,但他的著作和文章现在仍被广泛阅读和引用,部分原因是他仍然是少数几个撰写传统战争的民间战略家之一,在核均势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20大多数一流的民间战略家,尤其是那些更加资深的,大多关注核战略或相关主题。因此一个醉心于了解传统战争的学者很可能会沉浸在李德·哈特的作品中。李德·哈特还关心大战略——另一个现在仍可以吸引防御学者注意力的主题。21他深入参与到20世纪30年代的辩论中,关于英国是否应该接受大陆承诺或者采取经常被提及的“蓝海战略”。考察李德·哈特的思想可以为发生在美国的一场相似的争论带来有趣的洞见,这场争论是关于从欧洲撤回大量美国地面和空中战术力量,更加倚重美国海军阻止苏联进攻的优点。22考虑到外界对他经常被误读的理论的兴趣,澄清它们很重要。
考察李德·哈特的军事思想应该特别吸引研究军事的社会科学学者。虽然他是作为一位战略家或历史学家而知名,这当然是很合理的标签,但他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社会科学学者。他持续地对比事件、个体和情境,以发现可以经受时间和空间检验的一般性规律。塞缪尔·霍尔爵士的表述很有道理,即李德·哈特拥有“非英国式的归纳天赋”。23他寻求构建可以用来解决英国战略困境的一般性理论,大胆地陈述并固执地维护(这些理论)。作为一个有智慧和勇气的人,他在沉浸于当时的争论时,十分倚重他的理论。
研究李德·哈特的另一个原因是澄清历史记录的需要,尤其是因为学者们经常依赖他对历史的描述。评价李德·哈特的个人作用是评价英国和德国军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表现这个更大议题的一部分。那个时期的英国军事领导人,尤其是军队将领被广泛看作无能的,而德国的军事首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将军通常被大加称赞。他们建立了强大的装甲和空中攻击力量,这是因为他们输掉了上一场战争,而只有失败者才能从之前的战争中吸取正确的经验。2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将军没有受到像他们的后来者一样的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鲜有可挽回的价值;但他们受到的对待还是比英国的同伴要好得多。25主要原因是对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中所发展的进攻型步兵战术的关注。26
这些对两个军队的描述即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是过度夸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因发展出创新的步兵战术应该被认可,但同时英国人还创造了坦克,并且英国的将军十分愿意依赖这种武器,进而赢得战争。27另外,英国军队也乐于接受李德·哈特关于步兵战术的先进思想——事实上这与德军的思想十分相似。在领导力方面,即使我们不完全接受很受欢迎的历史学家约翰·特雷恩(John Terraine)对陆军元帅道格拉斯的辩护,他也比大众所认知的更加有能力。28他肯定比德军的四位战时领导人更加优秀,这四位领导人是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保罗·冯·兴登堡陆军元帅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29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英国和它的盟国赢得了战争。在两场战争期间,德国军事也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先进,快速翻阅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一点。他的回忆录显示,德军中对坦克战的先进观点有很强的阻力。相反地,英国军队绝没有普遍认知的那样死板。针对这点可以在布赖恩·邦德关于两场战争期间英国军队的研究中找到大量证据。30
还有很好的理由怀疑一些(外界)接受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想一下英法同盟在法兰西战役中的失败。毫无疑问法国和英国没能了解到坦克对战场的影响,在1940年5月采取了错误的战略。31事实上,英国军队几乎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然而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蒙昧,主要原因是张伯伦政府在1937年12月决定不为欧洲大陆建设一支军队,这个政策是李德·哈特坚定支持的。另外,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军队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这一政治决定的结果,这导致已经虚弱的英国军队在1937年12月到1939年初这段关键时期持续地弱化。至于德国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肯定有很多优秀的战场指挥官,因此德军经常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出色。32然而,我们不仅仅依靠战场表现评价指挥官,这些将军大部分愿意支持希特勒发动并扩大战争的决定。33他们要为后果承担责任,即他们的国土遭到破坏和分割。虽然作为战斗者他们获得胜利,但是作为大战略家他们得到的是灾难性失败。
德国国防军还应为纳粹政府的大屠杀政策负主要责任,尽管直到最近都很少被提及。事实上,德国将军通常被描述为有远见的指挥者,服从于一位对军事知之甚少但却总是将决定强加于他们的领导人,虽然他们知道这些决定会导致灾难性结果。这当然是李德·哈特在《德国将军访谈》一书中所持的观点。然而,现在看起来除了帮助希特勒进行扩张之外,德国国防军还参与了在西线对数百万平民和战俘的屠杀中。34
这本书不直接讨论(外界)对英国和德国军队的认知。然而,它涉及很多上文所讨论的议题,皆是因为李德·哈特在塑造这些认知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对两场世界大战的描述得到高度认可,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力。在这些以及其他著作中,他有说服力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元帅黑格和其他的英国将军是无能之辈。对于塑造大众对两场战争之间英国军队表现的认知,他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它的《回忆录》。在塑造英语世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国防军的看法方面,他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其他任何人。
李德·哈特的案例还指出了历史的脆弱性,以及对基于私利操纵历史的危险保持警惕的重要性。李德·哈特毕竟成功地使大多数学者相信他对20世纪30年代的描述是正确的,并且在那些记得两场战争之间发生了什么的人仍然在世的情况下,他却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另外,他写的并不是鲜为人知的事件,而是那些不断受到关注的重要事件。然而,他几乎完全成功地欺骗了所有人。
事实上,如果他没有强迫性地记录他自己的想法和行为,他的欺骗行为可能不会被发现,他的私人文件中保存了关于他行为的超乎寻常的完整记录,这却成为研究这个案例的进一步原因。我们很少能够精确地追踪某个人思想的发展,并判断那个人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作用,主要原因是人们几乎都只会留下不完整的记录。李德·哈特不断地写作并备份几乎所有他写过的东西,甚至是他文章的草稿。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还写了用作记录的备忘录并与几百人通信。35另外,李德·哈特认为他自己很重要,因此他记录了他思想发展的不同方面,所以要追踪他在两场战争之间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并且追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挽救声誉所做的努力就相对容易很多。简单地说,他留下的文件为探寻一个重要人物的人生故事提供了一个独特窗口。
最后,考察李德·哈特的经历可以进一步了解国防学者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尽管平民战略家主要是核时代出现的现象,李德·哈特与汉斯·德尔布吕克、朱利安·科贝特以及斯宾塞·威尔金森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平民防务专家。李德·哈特是英格兰或者说美国第一个非军方思想家,他对军事问题的观点广受公众关注并且得到当时军事机构的认真考虑。另外,他还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核威慑思想的发展。36任何人如果关注外部专家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不管是在核时代还是非核时代,都会从李德·哈特的经历中受益匪浅。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结局很糟糕。他从20世纪30年代一个重要的、备受尊重的权威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声誉严重受损的体制局外人。他的困境有两点现在值得注意:发展一致的、可行的军事理论是一项困难的工作,避免错误思想主导战略辩论的最好办法是知识多元化。一个健康的国家决策过程取决于有独立思想的防务知识分子能否质疑政府并且相互质疑。
李德·哈特的名字和思想在大量的著作和文章中都被提及,很少有军事问题学者没听说过他,然而关于他的文献却很稀少。只有两项研究是关于他在两场战争之间的经历和他军事思想的发展:杰伊·卢瓦斯在他的《军队的教育》(1964年)中关于李德·哈特的章节(“教导将军的上尉”),以及布赖恩·邦德的《李德·哈特:对他军事思想的研究》(1977年)。还有少量很好的文章是关于李德·哈特生活中的细节。371970年1月他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打算出版一本他的传记,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有写,并且很明显没有将此委托给别人的计划。38
这本书如何能够超越卢瓦斯和邦德的作品?卢瓦斯的那篇文章只是书中的一章,无法提供关于李德·哈特的主要思想或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辩论中的作用的综合和细致的考察。更重要的是,这一章实质上只是对李德·哈特自己版本的概述。卢瓦斯是李德·哈特极其亲密的朋友,他对李德·哈特的批评很少。为了与李德·哈特保持一致,他提供的是对他军事思想和政策建议的歪曲描述。而邦德的著作是一流的研究作品,既全面又富有洞见,任何想要理解李德·哈特军事思想的人都应该认真研读他的著作。事实上,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是站在邦德的肩膀上。
然而在一些要点上,邦德对历史的描述应该被修正。例如,邦德否认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德国的将军挽救他的声誉,我认为这是错误的。39我还认为,邦德错误地接受李德·哈特的说法,即他是绥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40另外,我不同意他的这一说法,即“很难确定李德·哈特是否准确地预测到1939年和1940年军事事件的”。41尽管有很多不同之处,我的作品不应被视为对邦德著作的质疑,而是超越他的分析的一个尝试。邦德的著作也没能充分地批评李德·哈特。尽管他提出了很多明显的批评,他并没有推出合理的结论。他在书中本可以更加有力地驳斥(哈特),但却没有充分展开。42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在邦德的书中没有被讨论或者仅仅被提及。例如,邦德没有讨论李德·哈特是如何挽救他的声誉的。尽管在他的书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一些传统认知是有缺陷的,但他没有解释这些扭曲是如何产生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他没有直接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两场战争之间,李德·哈特就深层战略穿透写了什么内容,这是闪电战的核心。他也没有系统地考察李德·哈特关于应对第三帝国的政策建议的后果。我试图讨论这些以及其他邦德忽略的问题。
这个研究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李德·哈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将军能力的思考直接影响了他的大战略思想的发展,这反过来影响了他对战略和战术的思考。因此必须尽可能精确地定义这些概念,因为它们经常会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
战略是关于如何在战区部署和调动军队全部的重要作战单元和支撑性的空中战术力量,以实现总体的战役目标。换句话说,战略关心的是组成一场战役的不同战斗是如何连接在一起,以实现理想的军事效果。战术是一个关注点更加狭窄的概念:关注重点是具体战场上如何利用军队的不同要素及空中支援力量。战术讨论的是如何使用具体的军事要素赢得某场战役。为了说明这些概念,可以想一下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穿过法国进入德国的案例。战略问题围绕的议题是如何使用组成盟军总体力量的不同军种和军团,尽可能迅速地打败德军。战术问题关心的是军队中更小作战单元的个体行为,从排到军团。在这个研究中,战略与闪电战和装甲战相关联;战术等同于部署小规模的步兵单元。
大战略包含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国外主要的军事威胁是什么,应该如何排序?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对海外的防御承诺进行排序?第二,一个国家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军事力量以支撑这些承诺?现有的军事手段很自然地会影响承诺的规模和范围。这里使用的大战略概念不是关于一个国家如何整合所掌握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工具以维护其海外利益。尽管有时大战略是这么定义的,这个概念在这里的定义稍微狭窄,即军事手段和国际承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外交或经济手段没有军事手段重要。事实上,正如这里所定义的,外交政策的广义含义都是关于对这三种手段的整合以支撑海外承诺。尽管关注点是李德·哈特对大战略、战略和战术的思考,在分析他对第三帝国的观点时,有必要考虑他对广义外交政策问题的思考。
在整个20世纪英国的大战略辩论中,是否作出大陆承诺曾经是一个中心话题。43大陆承诺意味着派遣大量军队到欧洲大陆,防止一个竞争性对手控制欧洲大陆。在20世纪之前,英国能够用规模适中的军队支撑大陆承诺。它用强大的海军、经济力量和对大陆盟国的高度依赖弥补相对较小的陆地力量。44到20世纪初,英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军队以面对大陆力量的挑战。因为英国传统上维持小规模的常备军队,这一发展对它的国家安全机构的规模和形态,尤其是它的军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简单地说,作出大陆承诺的核心问题是规模、形态和英国军队的目标。45
接下来的五章将描述并评估李德·哈特在1918年至1945年之间的军事思想,并解释这个发展过程。第二章关注1919年至1924年间的李德·哈特,这段时间他发展了步兵战术理论,并形成了关于闪电战的理念。第三章考察他对英国将军不断增强的幻灭感,尤其是针对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第四章的主题是关于1925年至1932年间他提出的间接路径理论,并对战争中的英国方式进行概述。第五章和第六章关注1933年至1940年,在这段关键时期,英国面对与德国进行一场大规模陆地战争的严峻前景。这里将考察他关于英国应该如何应对第三帝国的观点。第五章集中关注他在这些年中的军事思想。第六章关注他在广义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第六章还包括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困境的简要思考。这五章的讨论融合了叙事和分析。我本倾向于将这两部分分开,但是这个主题不适用于这样的分割。
尽管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关于李德·哈特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有很多内容,但仍有必要用整个第七章讨论这个主题。第八章是关于李德·哈特如何在战后恢复了他的声誉。最后,简短的结论部分将从这个案例中吸取一些教训。
注释
1. Alastair Buchan, “Mechanized Warfare,” rev of Memoirs, vol.1, by LH, New Statesman, 4 June 1965:887; Michael Howard, War and the Nation State(Oxford: Clarendon, 1978), 7; A.J.P. Taylor, “Soldier Out of Step,” rev of Memoirs, vol.1, Observer Weekend Review, 30 May 1965, 26; Jay Luvaas, LH's obitua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June 1970): 1573; John F. Kennedy, “Book in the News,” rev. of Deterrent or Defense, by LH, Saturday Review, 3 Sept. 1960, 17.
2. 古德里安和曼陀菲尔的引证来自Memoirs, vol.2(London: Cassell, 1965), btwn. 194 and 195的内图。阿隆和沙龙的引证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李德·哈特军事档案中心展示的图片。
3. 关于李德·哈特的早期生涯,参见他的“Forced to Think,” in George A.Panichas, ed., Promise of Greatness: The War of 1914—1918(New York: John Day, 1968), 98—115; Memoirs, vol.1, prologue and chap.1; Brian Bond, Liddle Hart: 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London: Cassell, 1977), 12—27。1921年,他将他的姓由哈特改为李德·哈特(李德是他母亲的姓氏);参见B.Bond, Liddle Hart, 12, 34。
4.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李德·哈特的说法(Memoirs 1:64—65),即他被迫退役的原因是他的观点不受欢迎。
5. 战术、战略与大战略这些术语将在下面给出定义。
6. 豪斯与汉密尔顿的引证来自“Tributes and Testimonies,” 13/2;劳合·乔治的引证来自Memoirs 1:362; John Buchan, “General W.T.Sherman,” rev. of Sherman: The Genius of the Civil War, by LH, Spectator, 15 Mar. 1930, 436. J.F.C。富勒, 另一位那个时代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对将李德·哈特比作克劳塞维茨有不同观点:“有人称他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当然,如果要做一个比较,他与弗朗西斯·培根这样富有思想的实证哲学家更加接近,因为他关注事实而不是想象。”(“Mechanical Warfare,” rev. of 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 by LH, English Review 55, Sept.1932:337.)
7. 例如,参见Irving M.Gibson, “Maginot and Liddle Hart: The Doctrine of Defense,” in Edward Mead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365—387。
8.The Real War, 1914—1918(London: Faber, 1930);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Cassell, 1970).关于李德·哈特著作的完整书单,包括每本著作的不同版本,参见B.Bond, Liddle Hart, 227—278。
9. Foch: The Man of Orleans(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31); Sherman: Soldier, Realist, American(New York: Dodd, Mead, 1929).
10. The Tanks, 2 vols.(London: Cassell, 1959).
11.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London: Cassell, 1948),同时在美国出版的版本是The German Generals Tal(New York: Morrow, 1948);修订与扩展版是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London: Cassell, 1951)。
12. The Rommel Papers, trans. Paul Findla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3); T.E.Lawrence in Arabia and After(London: Cape, 1934),在美国出版的版本是Colonel Lawrence: The Man behind the Legend(New York: Dodd, Mead, 1934)。
13. 参见B. Bond, Liddle Hart, chap.7; 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New York: St. Martin's, 1981)。
14. 李德·哈特关于核战略与北约的主要著作是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London: Faber, 1946); Defence of the West(London: Cassell, 1950); Deterrent or Defence(London: Stevens & Sons, 1960)。
15. 在发展关于防御者战场优势的观点时,李德·哈特提出了关于力量与空间比例概念的重要洞见,这被认为是他在两场战争之间发展的第六项重要的军事思想。他(的思想)还高度依赖“进攻-防御平衡”概念,这是另一个获得持续关注的课题。
16. B. Bond, Liddle Hart, 90.
17. A.J.P. Taylor, “A Prophet Vindicated,” rev. of Memoirs, vol.2, by LH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 ed. Michael Howard, Observer, 31 Oct. 1965, 27. Copies of all the reviews in 9/30/38—44.两个很重要的评论,参见Col. Trevor N.Dupuy, “The Selective Memoirs of Liddle Hart,” rev. of Memoirs, vols.1 and 2, Army 16(Aug. 1966):36—38, 81; Barry D.Powers, rev. of Memoirs, vols.1 and 2,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0(Dec. 1968):630—631。
18. Michael Howard, “Englishmen at Arms,” rev. of Memoirs, vol.1, Sunday Times, 30 May 1965, 24.
19. Statement of the Hon. G. William Whitehurst, Washington, D.C., 14 Dec. 1981, 30.
20. 例如,美国陆军的空地战学说发展,在军队的作战手册课程中得到详细阐释,Operations: FM 100-5(Washington, D.C., Aug. 1982);这份文件的主要作者之一描述了李德·哈特的作品如何深刻影响了学说的发展:Huba Wass de Czege, “Army Doctrinal Reform,” in Asa Clark et al., eds., The Defense Reform Debate(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1—120;另参见Operations: FM 100-5, 8—6, 9—1, A3。
21. 战略核(力量)对等(话题)提升了对常规威慑兴趣的上升,同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相对下降,加上美国外交承诺的不断增加(主要是波斯湾地区),使得大战略受到极大关注。
22. 关于大量的文献,可参见Keith A. Dunn and William O. Staudenmaier,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Continental-Maritime Debate. Washington Paper No.107(New York: Praeger, 1984); Robert W. Komer, Maritime Strategy or Coalition Defense(Cambridge, Mass.: Abt Books, 1984); Christopher Layne, “Ending the Alli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tudies 6(Summer 1983):5—31; Earl C. Ravenal, “The Case for Withdrawal of Our Force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6 Mar. 1983, 58—61, 75。
23. 引自Brian Bond, “Second Thoughts on War: A Conversation with B.H. Liddle Hart,” Military Review 45(Sept. 1965):29。关于李德·哈特回应一个批评者对一般性理论价值的质疑,见Lt. Col. L.V. Bond, “The Tactical Theories of Captain Liddle Hart: A Criticism,” Royal Engineers Journal 36(Sept. 1922):153—163; LH, “Colonel Bond's Criticism: A Reply,” ibid.(Nov. 1922):297—309。
24. 李德·哈特早在1925年就提出这个观点,他写道:“国家从失败中比从胜利中学到的东西更多,这是一个真理,尽管德国暂时被禁止发展坦克,它的战后军事回顾以及教科书充分证明了关于它们战术的研究。”(“After Cavalry-What?” Atlantic Monthly 136 Sept. 1925:415.)
25. 可以思考以下这些流行著作的标题:Col. Trevor N. Dupuy, A Genius for War: The German Army and General Staff, 1807—1945(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Donald J.Goodspeed, Ludendorff: Genius of World One(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6)。很难想象一个作者会在英国军队身上使用“天赋”这个词,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军队指挥官。
26. Timothy T. Lupfer, The Dynamics of Doctrine: The Changes in German Tactical Doctrin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Leavenworth Paper no.4(Fort Leavenworth, Kans.: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July 1981).
27. 参见Robert H. Lawson,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Theory of Armored Warfare, 1918—1940(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4), chap.2; John Terraine, Douglas Haig: The Educated Soldier(London: Hutchinson, 1963), 95, 220—228, 289, 360, 362, 378, 381, 448—449, 453。
28. 参见Terraine, Douglas Haig; idem, The Western Front, 1914—1918(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5); idem, To Win a War: 1918, the Year of Victory(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1)。
29. 关于这些指挥官的缺点,参见Correlli Barnett, The Swordbearers: Supreme Command in the First World War(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aps.1, 4。
30. 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trans. Constantine Fitzgibbon(London: Joseph, 1952), esp. chaps.2—5; Brian Bond, British Military Polic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1. 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3。
32. 关于德国军队战斗力水平被夸大的事实,参见John Sloan Brown, “Colonel Trevor N. Dupuy and the Mythos of Wehrmacht Superiority: A Reconsideration,” Military Affairs 50(Jan. 1986):16—20。
33. 三个关键的(战争)决策是波兰(1939年),法国(1939—1940年)和苏联(1941年)。一些将军明确反对入侵波兰和法国,但对入侵苏联几乎没有异议。参见Matthew Cooper, The German Army, 1933—1945(New York: Stein & Day, 1978), pt.3; Barry K. Leach, German Strategy against Russia, 1939—1941(Oxford: Clarendon, 1973);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chap.4; Telford Taylor, The March of Conquest: The German Victories in Western Europe, 1940(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8)。
34. 德国与英语世界的学者毫无疑义地表明,事实上德国国防军在德国的屠杀机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参见Omer Bartov, The Eastern Front, 1941—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New York: St.Martin's, 1986); Christopher R. Browning, “Wehrmacht Reprisal Policy and the Mass Murder of Jews in Serbia,” Milita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no.33(1/1983):31—47; Jurgen Forster, “New Wine in Old Skins? The Wehrmacht and the War of ‘Weltanschauungen,’ 1941,” in Wilhelm Deist, ed., The German Militar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Dover, N.H.: Berg, 1985), 304—322; idem, “The Wehrmacht and the War of Exterminatio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Yad Vashem Studies 14(1981):7—34;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vol.1(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5), 273—390; Helmut Krausnick and Hans-Heinrich Wilhelm, Die Truppe des Weltanschauungskrieges: Die Einsatzgruppen der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s SD 1938—1942(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1); Henry L.Mason, “Imponderables of the Holocaust,” World Politics 34(Oct. 1981):90—113; Christian Streit, Keine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1941—1945(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8)。
35. 关于李德·哈特浩繁的私人文件,参见Stephen Brooks, “Liddle Hart and His Paper,” in Brian Bond and Ian Roy, eds., War and Society: A Yearbook of Military History(London: Croom Helm, 1977), 2:129—140。
36. 德尔布吕克(1848—1926年),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学者与记者,他可能是第一位对大众思考军事事务产生广泛影响的平民战略家。关于他的两部最好的英文著作是Richard H.Bauer, “Hans Delbrück,” in Bernadotte Schmitt, ed., Some Historians of Modern Europ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100—129;以及Gordon A.Craig, “Delbrück: The Military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326—353。科贝特(1854—1923年)与威尔金森(1853—1937年)是之前受到李德·哈特推崇的英国“平民战略家”;分别参见Donal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1867—1914(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chap.7;以及Jay Luvaas, The Education of an Army: British Military Thought, 1815—194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chap.8。尽管“平民战略家”对李德·哈特来说是一个恰当的标签,但他毕竟在英国军队服役十年。关于后来的“平民战略家”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早期核战略发展中的作用,参见Gregg Herken, Counsels of War(New York: Knopf, 1985);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Barry Steiner, “Using the Absolute Weapon: Early Ideas of Bernard Brodie on Atomic Strateg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7(Dec. 1984):365—393。
37. 关于两场战争之间的李德·哈特,参见Luvaas, Education of an Army, chap.11;还参见The Military Legacy of the Civil War: The European Inherita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216—225。还参见Brian Bond and Martin Alexander, “Liddle Hart and DeGaulle: The Doctrines of Limited Liability and Mobile Defense,” in Paret,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598—623。Earl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中有一章内容讨论李德·哈特(参见Gibson “Maginot and Liddle Hart”),这一章中有很多小的事实错误,但却提供了关于李德·哈特在两场战争之间观点的生动观察。李德·哈特就这一章内容与厄尔进行了大量的通信。尽管如此,这一章内容用处有限,因为它仅讨论了李德·哈特军事思想的一些方面,没有充分讨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关于李德·哈特生活的其他方面,参见Tuvia Ben-Moshe, “Liddle Hart and the Israel Defence Forces: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6(Apr. 1981):369—391; Brian H. Reid, “T.E. Lawrence and Liddle Hart,” History 70(June 1985):218—231; idem, “British Milit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F.B. Maurice, J.F.C. Fuller and B.H. Liddle Hart,” in Chris Wrigley, ed., Warfare, Diplomacy and Politics: Essays in Honor of A.J.P. Taylor(London: Hamilton, 1986), 42—57。
38. 与布赖恩·邦德的通信,24 Sept. 1987。
39. B. Bond, Liddle Hart, chaps.6, 8, esp. 166, 188, 228.
40. Ibid., 102, 112.
41. Ibid., 114.
42. 邦德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对李德·哈特有更多的批评,British Military Policy;参见我的评论文章“The British Generals Tal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6(Summer 1981):165—184。
43. 参见Michael Howard, 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 A Reappraisal, The 1974 Neale Lecture in English History(London: Cape, 1975); idem, The Continental Commitment: The Dilemma of British Defence Policy in the Era of Two World Wars(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 Lane, 1976)。
44. 参见Kennedy, Rise and Fall, chaps.1—5; John M.Sherwig, Guineas and Gunpowder: British Foreign Aid in the Wars with France, 1793—1815(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45. 关于大陆承诺如何影响英国军队,参见Bond, British Military Policy;另参见Mearsheimer, “British Generals 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