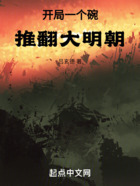
第12章 民乱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这是一句有名的农谚,说的就是冬小麦的种植。
在北方,青黄不接的时节指的就是这时候。
一路上,李弘问了许多正在播种的农民,都说今年年景不好,收上来的粮食连租子都交不上,更别说填饱肚子。
李弘也略微观察了一番,没发现有收种玉米的痕迹。
玉米在明末时便已经传入中国,而且传入的途径应该还不止一个,从各地对玉米的叫法就可以看出来。
南方主要由海路传入,称之为苞须、玉茭子。
北方主要经丝绸之路进入西北,叫苞谷、棒子等。
最早在嘉靖十年,玉米就经由印度传入了中国西南,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重视。
老百姓是用肚子投票的,到了两百年后的乾隆年间,玉米已经成了北方人民的主要口粮之一。
但是在李弘现在所处的时间点,玉米明显还没有广泛种植。
不然北方田地玉米春种秋收,小麦秋种春收,一年可以两熟。
只要不是大灾年份,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也不会产生这么多流民。
行至一个茶摊,一行人坐下来歇息。
李弘一边喝茶,一边思考着接下来的打算。
赶路的这几天他又试探着问了问杨算,知道他来自弘农杨氏的一个旁支。
弘农杨氏也算是千年世家了,不管家族支系散布在哪里,都自称来自弘农华阴。
就像杨算在这这一支,在汉中府发展,距离华阴县几百里的路,也还是自称弘农杨氏。
不过到他这一代,家族早就没落了,连个举人都没有。
其他支系其实也一个样,而且还不一定之支系,攀附的杨氏恐怕比真正的弘农杨氏还要多。
这也是杨算早年间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却只能当幕僚而捞不到官身的直接原因,没有功名。
投靠这样一个没落家族,对自己未来的帮助真的有用吗?
但是自己带着妹妹要想在明末乱世里独立生存下去,的确又有点困难。
如果是个盛世,李弘还可以自信能做到小富即安。
但这里是崇祯元年的陕西,矛盾总爆发的起点。
小冰河期的名头他是听过的,接下来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气候会越来越恶劣,土地兼并、粮食危机引发的矛盾大爆发会越来越激烈。
而在原本的历史道路上,这种影响一直要到康熙末年才会慢慢好转。
满清不是真的运气站在他们那边,而是人都被杀光了,人地矛盾自然就缓解了。
等到乾隆末年再次人口爆炸,社会矛盾再次激化。
只是不巧,再过几十年到来的不是全国性的大起义,而是殖民者的坚船利炮。
得想办法说服父子俩跟着自己干才行。
另一边,杨算接过杨戌递过来的银钱。
除了茶水钱,杨算又摆了几枚铜钱在桌上,问道:“店家,前面可有歇脚过夜的地方?”
店家忙过来把铜钱一一捡起收进怀里,陪笑道:“好教客人知道,前后客栈可远得很,但再往前走十里路有一村子,唤做赵家庄,那儿有个赵老爷是个心善的,客人可以去赵老爷那儿问问能不能留几位过夜。”
杨算拱手道:“多谢店家。”
随后,一行人收拾好行李,继续往前。
歇一夜,明日就能到西安府的治所长安县了。
……
另一边,李弘一行离开之后的咸宁县外城。
王三儿不仅没抢过那些个饥民,还被饿急眼又没抢到干粮的饥民们煮着吃了。
饥民们都是逃难的乡里乡亲,真要吃人心理上还过不去那一关,但王三儿不一样,这家伙是本地的。
字面意义上的吃人,在古代王朝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扰动,在咸宁县原本还算平静的水面上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涛。
闻到肉味的饥民再也受不了,开始在外城大抢特抢。
本身耕地就被用来建了房子,外城居民哪儿还有什么余粮?
饥民们找遍了所有能藏粮食的地方,也没找到多少可以吃的东西。
外城居民在惊慌之下一起向内城逃去,饥民们跟着一起往城里涌。
不管是抢劫的饥民还是被抢逃难的良民,一股脑地被巡检兵轰了出去。
很快,便有个自称震山响的家伙站出来领导饥民们去乡下抢粮食。
天灾导致土地歉收,佃农交不起租子被迫逃荒成为流民,流民进不了大城只能去抢劫还有余粮的农民,被抢的农民没了粮食也被迫逃荒……
越聚越多的流民最终走向造反的道路。
西北农民大起义,农民军如同核聚变链式反应一样爆炸式增长。
但没什么战斗力。
农民军真正开始攻城略地占领县城府城是因为农民逃荒没人生产粮食,大明中央朝廷也拿不出钱来给西北边军发饷,没钱没粮的边军也加入了农民起义的大队伍。
只不过此时此刻,咸宁城外这一批由震山响领导的流民群体还只能去乡下抢一下土豪。
李弘还不知道自己临走前借刀杀人的手段引起了多大的反应,只是赶着在天黑之前到达了赵家庄,一番问路之后,敲响了赵老爷家的大门。
李弘也想过就在庄子里的一般人家借宿,毕竟赵老爷作为本地地主不一定愿意收留外人。
但在庄子里接连问了几家都不愿意借宿,好不容易有一家人愿意,但只有一张床,睡不下四个人。
四人只好去往赵家大宅。
“谁呀?”门子的声音从大门里边传来。
咸宁城外有流民聚集的消息早就传到了赵家庄,庄主紧急给家丁配了武器,又吩咐门子每天提前关门。
今天门子刚把门关上拴好就有人敲门,问询的语气当中透露着些许不耐烦。
杨算语气里带着些许歉意答道:“过路的旅人,想在贵宝地借宿一宿。”
门子一听这话不高兴了,态度也更差了些,道:“这里又不是客栈,快走快走。”
李弘从盐罐子里取出一粒碎银从门缝里塞进去,接着又往里边喊道:“这前后客栈太远了,我等夜里赶路怕不安全,还望通融一二。”
递银子的时候李弘心都在滴血,如果不是零钱都花光了加之走得匆忙,他哪里会为了贿赂一个乡下看门的给一粒银子出去。
门子收了钱,把门打卡一条缝,露出一只眼睛从缝里看了看,确认只有四个人,而且只有一个成年人,似乎没什么威胁。
“客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啊?”
门子站在门内,把门缝稍微开大了些。
“我们从山西探亲而来,往汉中府返乡去的。烦请与赵老爷通禀一声,我们只住一宿,明早便启程,这是食宿的钱。”
然后李弘又递过去一粒碎银。
门子接过钱,道:“行,等着吧,我去禀告老爷。”
没多久,门子便笑呵呵地开了门,道:“贵客请进。”
一行人进屋,门子正要关门,却见远远地看见有一人跑过来,离近了还能听见呼声。
“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啦。”
门子赶紧把那人接进屋内,责问道:“吵吵嚷嚷什么?老爷交代的事情你办好没?”
那人喘着粗气道:“不……不好了……乱民……乱民抢了县城,朝……朝庄子这边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