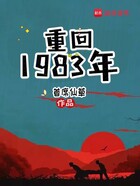
第66章 礼堂开会
众人听闻老支书的发言,脑袋凑在一块儿,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礼堂里一时间嗡嗡作响,好似炸开了锅。
片刻后,刘有义“噌”地站起身,扯着嗓子大声问道:
“支书,要是一家有好几块田都得被挖,这补偿是分开算,还是咋算呐?”
明眼人都瞧得出来,刘有义家有两块地紧挨着马路,他这般发问,无非是担心自己只能拿到一份补偿款。
老支书不紧不慢地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方瞅了刘有义一眼,稳稳地说道:
“甭管一家有几块田要让地,补偿都是按让出的总公分来算。”
刘有义听了,暗自琢磨一番,脸上浮起一抹满意的笑意,缓缓坐了下去。
此刻,他心里早已经盘算起这笔即将到手的补助款该怎么花了。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以他那对王美丽上心的劲儿,十有八九会拿去给王美丽扯几尺“的确良”布料。
这时,另一位村民刘天远站起身,清了清嗓子,说道:
“让地这事儿,大家都没意见,我也没啥说的。不过,这水径开口子引水的事儿,可得讲明白咯。别到时候水径修好了,我们这些下游的田却分不到水,那可就白忙活一场了。”
刘天远在刘姓家族里辈分颇高,平日里说话就有分量。
他这一开口,不少人纷纷点头称是。
“刘老爹这话讲得在理呐,像我们这些离马路远的,每次分水都得看前面几家的脸色。要是不多开几个口子,到时候为了争水,说不定真得打起来。”
一位村民连忙附和道。
“是啊是啊,咱们那些田,要是分不到水径的水,那这水径修了有啥用?还不如咱们自己多架几根竹子引水呢。”
又有村民跟着大声说道。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热火朝天,情绪愈发高涨。
老支书瞧着场面渐渐有些失控,赶紧伸手用力拍了拍喇叭,扯着嗓子高声喊道:
“都静一静!”
“这水径开口子,可不是随随便便想开哪儿就开哪儿,不然整条路不就成了老鼠洞,到处漏水啦?”
“村上的意思是,每隔十米开一个口子。要是碰到溪水穿过马路的地方,就以溪水穿过的地方为基准来算。”
“那可不行呐!”一位村民“嗖”地站起身,情绪激动,满脸涨得通红,
“野鸡岭出来的那条溪,水面比田埂矮了几十公分,从那儿引水,哪有从马路上的水径引水方便?我家的田就在那溪水边上,要是按村上这意见,我家两头都取不了水,这不是要断了我家的活路嘛!”
“对呀!”一位妇女也站起身,急得满脸通红,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我们亭子边上的田,溪水本来就少得可怜,根本不够分,哪有水径里的水多。要是不给我们开口子,那其他人也别想开!”
礼堂里的气氛剑拔弩张,大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为了自家的利益争得面红耳赤。
宋向阳静静地坐在台下,默默地听着这场激烈的争论。
他心里清楚,大家都只盯着眼前的小利,却忽略了村子长远的发展。
他在心里暗自琢磨着,到底该如何才能说服大家,让水径的修建以及马路的规划更具长远眼光。
正想着,寡妇王美丽不知怎的,突然站起身来:
“那个……这次左边的水径是不是也要修一下啊?那水径到处都漏水,水还没流到我们下面就没了。”
刘有义一听王美丽开了口,眼睛一亮,赶忙站起来帮腔:
“就是啊!右边修得那么好,左边却不管不顾,这像话吗?”
实际上,他家的田都在左边,可这左边修不修,本和他没啥直接利益关系,纯粹是想在王美丽面前表现一番。
王美丽见刘有义为自己说话,脸颊微微泛红,有些不好意思地瞥了他一眼,便匆匆坐下。
众人瞧在眼里,心照不宣,嘴角都忍不住微微上扬,这里面的门道,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不过,听两人这么一说,一些左边有田的农户也坐不住了,纷纷站起来支持:
“对,要修就两边一起修!都是村里的钱,凭啥只照顾右边,把左边当后娘养的?”
“我们左边的田,以前在生产队的时候就干旱得厉害,收成差得很。现在虽说分田到户了,可要是还没水,这日子可咋过?谁要是不同意一起修,到时候我家几个饿着肚子的崽子,就到他家门口讨米去!”
“就是啊,要修就一起修!不能厚此薄彼!”
众人的情绪被点燃,场面再度热烈起来。
台上的村干部们见状,纷纷凑到一块儿,交头接耳地商量起来。
老支书原本站着,这会儿也坐了下来,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讨论,时不时微微点头,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老支书才站起身,拿起喇叭,大声说道:
“大家静一静!经过村支部商量,决定左边的水径也一起修。”
“不过,这出工的事儿得说清楚。”
“没有田在马路边上的,出一天工给两毛钱;有田在两边的,一天给一毛钱。”
“反正现在农活也不忙,大家出个几天工,这水径就能修好。”
台下顿时又响起一阵议论声,不过这次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在了工钱的多少上,反倒之前争论不休的左右水径修不修的问题,讨论的少了。
宋向阳瞧着话题越跑越偏,心里有些着急,赶忙站起身,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镇定,声音洪亮有力:
“各位,修路和修水径,这都是为咱村子好的大好事儿。不过,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村里。”
宋向阳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目光认真地看向老支书。
老支书回给他一个眼神,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一旁的刘开盛脸色却有些难看,眉头微微皱起,似乎觉得宋向阳又要搞出什么幺蛾子。
宋向阳没理会刘开盛的态度,提高音量接着说道:
“这水径和路都是紧挨着的,修好了水径,那马路的宽度基本就定下来了。”
“但大家看看,咱们现在这马路,平时过过马车、赶赶牛,倒也还够用。可只要林场的车子一来,人就得赶紧从马路上躲到田埂上去。要是板车碰上林场的车,人还得把板车搬到田里,才能给人家让路。”
他微微转身,面向台下的村民:
“等林场把路修好,以后车子肯定越来越多,咱们出行可就更不方便了。更别说赶集和交公粮的时候,那不得堵得水泄不通?”
“咱们这村子虽说地处山卡卡,眼下没啥赚钱的门道,可大家谁不想过上好日子,总不至于穷一辈子吧?”
“等以后日子好了,大家慢慢发展起来,说不定有人会买上手扶拖拉机、嘉林摩托,甚至是货车。”
“到那时候,这窄巴巴的马路,两辆车咋错车?难道每次都要把车开到田里去吗?”
宋向阳心里清楚,现在跟大家说以后人人都能买小汽车,还不太现实,大家也难以想象。
所以,他特意举一些大家平日里能看到、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样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让大家意识到拓宽马路的重要性。
而且,他心里明白,现在要是不把这路拓宽,等到将来政策一放开,允许在田里建房,大家肯定都一窝蜂地在马路边上修房子。
到那时候,村里再想拓宽马路,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更重要的是,要想发展经济,这路至关重要。
村里除了树可以卖,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有作为的地方。
只不过,很多时候都是被这路给限制了。
自己今后要想赚上更多的钱,更要依靠这路。
等着这条发财路修的更好,他还有一大堆计划要实施呢。
众人原本还在为两边修水径和工钱的事儿争论不休,听到宋向阳抛出这么一个全新的问题,瞬间又炸开了锅,七嘴八舌地讨论愈发激烈。
尤其是几个平日里喜欢来看电视的人,讨论的情绪极为高涨。
他们在电视里见过大城市的繁华,车水马龙的景象让他们印象深刻。
此刻,宋向阳的话也让他们有几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