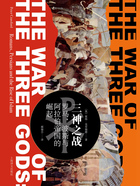
导言
公元七世纪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然而却被严重低估。其时所处阶段出现于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被轻描淡写地称作“黑暗时代”。此提法无疑措辞失当。在该术语所特指的西欧,这一时期并不黑暗,文化暗夜当然也未蔓延至东方。虽有盛衰起落,罗马帝国犹称雄地中海,而在中东,与之交锋最久的宿敌萨珊波斯帝国仍构成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七世纪的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未经巨变。最初三十载罗马与波斯再起干戈,或类乎以往数百年。东西军事对抗肇始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乃至更早,已延续多个世纪,而此战判然有别。因宿命使然,罗马与波斯的最新冲突不仅至为惨烈,且是终极对决。
长久以来,罗马—波斯战争仅为短时恶斗,却少有胜负,多无果而终。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罗马人与伊朗高原统治者虽断续交锋近七百年,双方边界却无大改。历次征战或规模小,或为时短,几乎未给两帝国造成变化。602至628年的战争则全然不同。此战中,大片领土易主近二十载,双方将上演政教阴谋,展开精心部署的大战与围城,致罗马帝国濒临覆灭。尽管在战火消歇时领土状况恢复如初,双方却因持久恶战而彻底改变:一方自此一蹶不振,另一方虽余八百年国祚,却前后迥然,后世史家只得易其名称。唯有战争可致此剧变,而促变之因还不止于罗马与波斯重启战端。希拉克略和库思老的交兵虽破坏巨大,所反映的七世纪情状却不足一半。二宿敌鏖战正酣而致两败俱伤之际,长期被认为专事贸易和袭掠的边陲荒漠正历经宗教巨变。
谈及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创立也许最广为人知,而善战信徒以新教名义实现的伟大军事征服却远不及前者闻名。受初建信仰激励,穆斯林先是一统阿拉伯半岛,继而对罗马和波斯的传统霸主地位发起挑战,并将之彻底推翻。先知穆罕默德逝后不到一代,经由一系列卓越战役和重大战斗,凭借政教上巧施宽容政策,伊斯兰教及信徒取得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军事征服之一,朝着完全改变中东乃至整个地中海地区、中亚、印度次大陆历史进程的方向跨出了重要一步。
七世纪带来了古典世界的落幕。
史料来源
七世纪极为重要,理当有大量宗教、世俗和考古史料存世。史料出自罗马、波斯、穆斯林、西欧或中国,来源众多。在罗马帝国,有狄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1)(Theophylactus Simocatta)的历史著作,他也许是普罗柯比(2)(Procopian)一脉最后一位史家;有皮西迪亚的乔治(3)(George of Pisidia)所写的政治诗歌,作者曾亲历626年君士坦丁堡围城战;有《复活节编年史》等匿名著作,或安条克的约翰(4)(John of Antioch)等人的残篇;有皇帝莫里斯一世所著的《战略》,该书不只述及罗马军队的组织,也谈到萨珊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的军队;有追述历史的书籍,如尼基弗鲁斯(5)(Nikephorus)和狄奥法内斯(6)(Theophanes)等后世史家之作;有尼基奥的约翰(7)(John of Nikiou)对穆斯林入寇埃及的亲历记载、亚美尼亚的《库思老历史》(作者被误认为是塞比奥斯(8)[Sebeos]),很久以后莫夫谢斯·达斯祖兰奇(9)(Movses Dasxuranci)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王国历史》等区域史籍则让人们对七世纪获得更多了解。
波斯虽盛行口头传统,但在库思老一世治下,后期萨珊著述繁荣一时,涌现出大量哲学、神学、医学、政治学著作。库思老二世继续推动著书立说,汇集伊朗的民族历史故事,辑成《列王传》。当然,除神话、传说、历史和通篇的娱乐色彩之外,该书亦给人以道德、社会、政治等诸方面教益,故应审慎对待。1同时须指出的是,对萨珊帝国及其宗教的了解多源自古迹、庙宇、钱币,而最重要来源当属沙普尔一世、纳尔西斯(10)(Narses)、大祭司克尔蒂尔(Kirdir)以及库思老二世的铭文和浮雕。2
阿拉伯文化也倚重历史的口口相传,而对阿拉伯人乃至整个世界而言,七世纪最知名、最重要的史料却是书面文献《古兰经》。该书不仅是伊斯兰教的基石,亦可用以还原该教初创时阿拉伯半岛的状况,正如《新约》可用以再现公元一世纪初朱迪亚(11)的情形。《古兰经》的笔法与伊本·伊斯哈格(12)(Ibn Ishaq)、拜拉祖里(13)(Baladhuri)、塔巴里(14)(Tabari)等人的存世著作有重大区别,原因或在于,直到建立自己的世界帝国后,阿拉伯人方充分认识到成文史的价值。
由于伊斯兰教外传,且罗马人依旧在意大利活动,东西方的远地史料亦可提供额外信息。中国文献述及波斯萨珊王朝最后数十年的境况以及穆斯林与中国之间的早期军事对抗,而《教宗名录》和助祭保罗(15)(Paul the Deacon)的著作等宗教文献记载有七世纪末或八世纪初西方诸国与罗马人以及后来伊斯兰征服者的冲突。
不过,七世纪的史料虽大量存世,但由于当时缺乏可比肩塔西佗(16)(Tacitus)、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17)(Ammianus Marcellinus)、普罗柯比等人的杰出史家,对其研究严重不足。该状况也许在罗马—波斯战争中体现最为显著:各事件已被基本证实,对许多重要战斗却语焉不详。数十年后,穆斯林文献对此有所弥补,却又出现新问题。尽管较之沙赫巴勒兹(Shahrbaraz)、沙欣(Shahin)、希拉克略的胜仗,对耶尔穆克(Yarmuk)、卡迪西亚(Qadisiyyah)等大战的记载要详细得多,但由于史籍为后世所撰,以口头讲述为据,故有欠准确,时序问题尤为突出,使得对先后事件的理解愈加困难。
为弥补众多知识空缺,早期穆斯林史家往往笔法夸张、大事渲染、描述重复,著作的可靠程度再被削弱,学者只得另寻独立佐证。遗憾的是,后世罗马史籍同样时序混乱,原因或在于,作者曾参考阿拉伯史料及口头讲述。后世罗马著述多有潜在的茫然情绪,似乎时过数十载乃至数百年,仍无法解释当初帝国的危局与宿命。不足为奇的是,七世纪的萨珊文献同样有失传或失真问题,或毁于穆斯林征服,或被阿拉伯学者擅用,因移译而走样。然而,史料虽有缺憾,但不应抹杀或无谓质疑其中的史实。唐纳、肯尼迪、霍华德—约翰斯顿等几位现代史家已竭尽所能,向世人证明这些文献可用以重构罗马与波斯的终极一战、伊斯兰崛起,以及整个七世纪的历史。3
拼写及术语
七世纪时局丕变,多种文化间的冲突以拉丁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中古波斯语、阿拉伯语等诸多文字载于史册,须确立拼写与地名规范。为此,笔者弃用希腊语,而沿袭罗马名更传统的拉丁化拼法,如采用Heraclius(希拉克略),而非Heraklios,采用Mauricius(莫里斯),而非Maurice或Maurikios。因转译希腊语和拉丁语后变化巨大,许多波斯与阿拉伯名字更难处理。最典型的例证或许是波斯皇帝库思老,其名Khusro拼法繁多:Khusrow,Khusrau,Khosrau,Chosroes,Xosro,Xosrov,不一而足。笔者坦承对这些文字一无所知,故并未试图遵循任何语言惯例,而是力求保持拼写一致,希望不会给读者造成人物或地点的识别困难。
笔者以为,即使在阿拉伯大征服后,罗马帝国的架构仍大体未变,尽管语言上未必如此,故使用“罗马帝国”代替“拜占庭帝国”的提法,例外仅见于其他作者的直接引文。再者,出现在主战区北部欧亚草原的各部落联盟究竟源自何族,笔者无意参与讨论。因此,首提这些民族时,对其渊源将附以简要说明,再使用“阿瓦尔人”“突厥人”等较传统或笼统的提法。至于穆斯林哈里发国家的部落构成,提法则更为笼统。在穆斯林扩张早期,对不同的阿拉伯部落有所提及,而当伊斯兰军队进入主战区后,则将之大致视作同一群体。
城邑和地区名多用古称,并附以现称或临近地名,以助识别;有些古称更为知名,则不附现称,如君士坦丁堡不再解释为今伊斯坦布尔。
当然,倘有讹舛,致读者疑惑,责任完全在我。
(1) 狄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七世纪初东罗马帝国史学家,被认为是晚古时期最后的史家,所著《历史》记述皇帝莫里斯在位期间(582—602)的史实。本书脚注除非特殊说明,否则均为译注。
(2) 普罗柯比(约500—约562),东罗马史学家,记载亲历和为自己熟悉的查士丁尼时代的内外政事,著有《查士丁尼战争史》《论查士丁尼时代之建筑》《秘史》。普罗柯比时代(公元六至七世纪)是东罗马首个修史时期,当时的史学家主要包括普罗柯比、阿加提阿斯·斯科拉丝蒂卡斯、狄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
(3) 皮西迪亚的乔治,七世纪东罗马帝国诗人、史学家,曾随希拉克略征战。
(4) 安条克的约翰,七世纪史学家,其著作仅有残篇存世。
(5) 尼基弗鲁斯(约758—829),君士坦丁堡牧首、史学家,著有记述602至769年东罗马帝国大事的《简史》。
(6) 狄奥法内斯(约752—约818),东罗马帝国史学家,所著《编年史》是关于七至八世纪东罗马帝国的重要史籍。
(7) 尼基奥的约翰,尼基奥(尼罗河三角洲西南古城)科普特基督教主教,生活于七世纪。
(8) 塞比奥斯,七世纪亚美尼亚史学家。
(9) 莫夫谢斯·达斯祖兰奇,亚美尼亚史学家,约生活于十一世纪。
(10) 东罗马帝国莫里斯时期的东境统帅、亚美尼亚裔将军。注意不要与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另一位宦官名将纳尔西斯以及后文的萨珊波斯国王纳尔西斯(293至302年在位)混淆。
(11) 朱迪亚,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区,今巴勒斯坦南部和约旦西南部。
(12) 伊本·伊斯哈格(约704—约767),阿拉伯史学家,最早辑录穆罕默德生平事迹的作者。
(13) 拜拉祖里,九世纪阿拉伯史学家,著有《伊斯兰国家之起源》。
(14) 塔巴里(约839—约923),阿拉伯史学家,《古兰经》注释家,著有《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15) 助祭保罗(约720—约799),伦巴第人、史学家,著有《伦巴第史》。
(16) 塔西佗(约56—约120),古罗马史学家,著有《编年史》和《历史》。两书分别记载公元14至68年以及公元69至96年的史实,现仅存残篇。
(17) 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约330—约395),古罗马史学家,著有《大事编年史》。该书记载公元96至378年间的罗马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