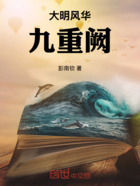
第2章 流火诏书
南京城闷热得像个蒸笼,文华殿檐角的铜铃纹丝不动。
朱允炆第三次抬头望向滴漏,青铜蟾蜍口中坠下的水珠却似比往常迟缓。他伸手扯了扯浆洗过度的龙袍领口,内衬的桑蚕丝早已被冷汗浸透——这是祖父朱元璋穿过的旧袍,袖口金线脱了三寸,像条垂死的蜈蚣趴在腕间。
“陛下,该进安神汤了。“太监王钺捧着漆盘跪在丹墀下。鎏金碗中映出少年天子苍白的脸,三十斤重的十二章纹衮服压得他肩骨生疼。
忽然一阵穿堂风掠过,十二幅《藩王镇边图》哗啦作响。朱允炆猛地站起,腰间玉组佩撞在御案角上,碎了一块谷纹璧。他的目光死死钉在燕王封地图那幅:狼居胥山用朱砂勾勒的轮廓,此刻在烛火下竟像道未愈的伤疤。
“黄先生到了么?“
“回禀皇上,黄学士与齐大人已在武英殿候了半个时辰。“王钺的声音细若蚊呐,“方孝孺大人说...说陛下若再不见,他就去太庙跪着。“
朱允炆的指甲掐进掌心。三天前同样的时辰,就是在这张龙纹填漆案上,黄子澄挥毫写下“削其羽翼,夺其根本“八字。当时窗外有只知了撞死在琉璃瓦上,碧绿翅膀粘在“燕“字朱批上,被他用镇纸碾成了齑粉。
戌时六刻,武英殿的冰鉴腾起袅袅白雾。
黄子澄的奏本在青砖地上摊开三丈有余,密密麻麻的官员名录像群蚁排衙。齐泰的佩剑随着踱步声叮当作响,这位兵部尚书正在复述济南卫的战报:“齐王府三百护卫尽数伏诛,缴获兵甲已押送凤阳...“
“可有活口?“朱允炆突然打断。
齐泰的剑穗僵在半空。烛光将他扭曲的影子投在《皇明祖训》匾额上,恰巧遮住“亲亲之谊“四个金字。“按陛下口谕,抗旨者...诛九族。“
殿角的青铜仙鹤灯爆了个灯花。朱允炆盯着自己微微发抖的手指,想起昨日在奉先殿看到的景象:太祖画像的眼角不知何时裂了道细纹,正斜斜指向燕王当年就藩时献上的青铜戈。
“燕藩那边...“少年天子刚开口,就被殿外喧哗打断。
方孝孺抱着半人高的奏折撞开殿门,苍苍白发间沾着夜露:“陛下!苏州府急报,白茆港的粮船被劫!“他的葛布直裰下摆沾满泥浆,显然是从通政司一路跑来的。
黄子澄的鼻翼微微抽动。他注意到最上方的奏折火漆是紫色——这是八百里加急的标志,但封套上的水渍却透着诡异的猩红。
“七月十七,太仓卫护送的十万石漕粮在长江口遇袭。“方孝孺的声音在发抖,“贼人用的是神机营的火铳,但留守卫所的兵符...三日前已随密诏送往北平。“
冰鉴突然倾覆,碎冰碴子溅到朱允炆的龙纹靴上。他想起五天前用印的那三道密诏:给济南卫的朱批是“霹雳手段“,给辽王的写着“骨肉情深“,而给燕藩的那封...那封本该由驸马都尉梅殷亲自送去!
“梅殷现在何处?“齐泰的剑鞘重重磕在金砖上。
“三日前离京北上。“黄子澄的喉结滚动,“按行程该到德州了,但...“他突然噤声,冷汗顺着脊椎流进玉带——那封给燕王的密诏,用的是不同于前两封的特制龙纹笺。
朱允炆觉得喉咙发紧。记忆突然闪回用印那夜:当他把第三封密诏交给梅殷时,殿外的梆子声恰好盖过了驸马的应答。现在想来,梅殷当时跪接诏书的姿势有些古怪,左手似乎始终缩在袖中...
“陛下请看这个。“方孝孺从袖中抖出一角焦黄的纸,边缘还带着燎痕,“这是从劫粮现场找到的,与兵部发给燕藩的文牍同出一批竹纸!“
齐泰抢过残纸对着灯细看,忽然踉跄着扶住蟠龙柱。纸面上隐约可见“燕王亲启“字样,但朱砂御印的位置却空着——本该盖印处留着个指甲盖大小的破洞,像是被火铳铅弹穿透的。
“梅殷...“朱允炆喃喃着跌坐龙椅。冰鉴的寒雾漫过他颤抖的手指,龙袍上的金线蜈蚣不知何时爬到了心口位置。
更漏声忽然变得震耳欲聋。黄子澄的奏折被穿堂风掀起,写着“燕山护卫指挥使张玉“的那页纸,正巧飘落在打翻的冰鉴上。墨迹在融冰中晕开,把“张玉“二字染成狰狞的血色。
子时三刻,谨身殿的蟠龙藻井渗出细密水珠。
朱允炆独自跪在太祖灵位前,手中的三支线香断了两次。供案上的和田玉圭突然裂开,那是朱棣去年进献的万寿节礼,内里竟露出半截生锈的箭簇。
“皇爷爷...“少年天子的呜咽淹没在雷声里。他想起半年前那个雪夜,自己偷偷翻开《太祖实录》,泛黄的纸页上记载着四叔朱棣十六岁率军奇袭乃儿不花的战绩。当时烛火将“燕“字的影子投在帷幔上,恍惚间竟似头欲扑的猛虎。
暗处突然传来衣料摩擦声。朱允炆警觉转身,却见王钺捧着个雕花木盒跪在幔帐后:“禀皇上,锦衣卫镇抚使求见,说是...说是找到了梅驸马的踪迹。“
盒中红绸上躺着枚鎏金纽扣,边缘沾着黑褐色的血渍。朱允炆认得这纽扣上的云雁纹——正是他亲赐给梅殷的驸马常服上的饰物。
“何处寻得?“
“通州码头往北三十里的芦苇荡。“镇抚使的声音像生锈的铁片摩擦,“现场有二十具烧焦的尸首,马匹的烙印是...是燕王府的形制。“
惊雷劈开夜幕,照亮朱允炆手中突然多出的短刃。这是黄子澄昨日进献的“忠孝匕“,说是用洪武朝缴获的蒙古弯刀熔铸而成。此刻刃面上映出他猩红的双眼,也映着北方某座正在熔铸铜钟的王府。
“传旨。“少年天子割下一缕头发扔进火盆,青烟扭曲成诡异的形状,“命耿炳文率十万大军进驻真定,让郭英把山海关的守军增加三倍。“他的指甲在太祖灵牌上划出深深的白痕,“还有,派人去北平宣旨——就说太后病重,请燕王即刻进京侍疾。“
同一轮明月下,北平燕王府的地窖却蒸腾着灼人热浪。
道衍和尚的袈裟被火星燎出无数破洞,手中人骨佛珠正在熔炉前泛着幽光。十二名铁匠赤膊捶打烧红的铜块,汗珠还未落地就化作青烟。
“加上这些铜钟,够铸多少门炮?“朱棣的声音从石阶上传来,玄铁甲胄上还凝着夜露。
“三百门佛朗机炮,再加五千枚开花弹。“道衍踢开脚边的铜佛头,那是从庆寿寺地宫挖出的北魏遗物,“足够把济南卫的城门轰成筛子。“
徐妙云忽然轻咳一声。王妃手中的桐油灯照亮角落:两个被铁链锁住的工匠正拼命摇头,满嘴鲜血直流——他们的舌头今晨刚被割去。
“王爷放心。“朱能拎着带血的麻袋进来,“这些匠人的家眷已安置在居庸关外。“副将的锁子甲上沾着新鲜血渍,“就是有个老家伙嚷嚷着要见姚广孝...“
道衍手中的佛珠突然绷断。老和尚弯腰拾起滚落的头骨珠,嘴角扯出古怪笑意:“故人相见,是该叙叙旧。“他转头望向朱棣时,眼中闪烁着二十年前在嵩山少林寺偷阅《武经总要》时的狂热,“王爷可愿随贫僧看场好戏?“
地窖深处的牢房里,白发老者被铁链吊在刑架上。当道衍的身影出现在火把光中时,囚犯突然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姚广孝!你这少林寺的叛徒!洪武二十三年空印案的余孽!“
朱棣的瞳孔骤然收缩。他看见道衍缓缓摘下僧帽,露出头顶十二枚戒疤——最上方那个疤痕形状诡异,竟与刑部大牢的烙铁印记一模一样。
“张侍郎别来无恙?“道衍的声音温柔得可怕,“当年你在刑部大牢给贫僧烙的这个印,说是能镇住妖僧的邪气...“枯瘦的手指抚过头顶伤疤,“不知今夜这场造化,可抵得过当年那方作废的空印?“
老者突然疯狂挣扎,铁链在石壁上擦出火花:“你会遭报应的!当年那三百官员的冤魂...啊!“
惨叫声中,道衍将烧红的烙铁按在老者胸前。焦糊味弥漫开来时,老和尚贴着囚犯耳朵低语:“知道为什么留你到现在吗?因为建文帝的削藩诏书...需要个合适的笔迹。“
朱棣握剑的手猛然收紧。他终于认出这个囚犯——洪武朝刑部侍郎张昺,五年前因卷入蓝玉案被太祖赐死,没想到竟被道衍偷梁换柱藏在此处。
寅时的梆子声穿透地牢时,道衍已将染血的宣纸铺开。张昺被铁链扯成跪拜姿势,右手被强行按在印泥上——这正是当年他在空印案中审讯道衍时用的手法。
“请王爷笑纳。“道衍呈上的密函字迹遒劲,赫然是建文帝亲笔:【朕感念叔父戍边辛劳,特赐双龙虎符,准燕藩扩军至十万...】
徐妙云突然捂住嘴。她认出落款处的玉玺印鉴,竟与丈夫珍藏的洪武朝旧诏一模一样——那方印,是马皇后临终前塞在朱棣襁褓中的。
“这是...“朱棣的指尖拂过伪造的圣旨。
“当年空印案留下的好东西。“道衍将人骨佛珠缠回手腕,“张侍郎恐怕到死都想不到,他私藏的空白钤印文书,会变成燕王殿下的东风。“
地牢外忽然传来急促脚步声。世子朱高炽捧着《春秋》跌跌撞撞冲进来,书页间飘落张染血的信笺:“父王!应天急报!皇上...皇上要您进京侍疾!“
朱棣接过信笺就着火光细看,突然放声大笑。笑声震得地牢顶部的土石簌簌落下,惊起成群蝙蝠。“允炆这孩子,倒是学会他父亲的仁厚了。“七星剑铿然出鞘,将信笺钉在刑架上,“告诉张玉,三日后拔营!“
道衍正用朱砂笔在伪造的圣旨上添加最后几笔。老和尚的瞳孔映着熊熊炉火,轻声哼起二十年前在诏狱里听过的秦淮小调。在他脚边,张昺的尸体渐渐冰冷,胸前烙痕赫然是“靖难“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