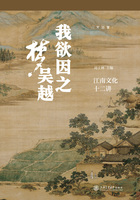
绪论 人人尽说江南好
从2000年开始,我们团队就开始研究江南,研究范围涉及江南文化、江南美学、江南城市和作为传统江南地区当代形态的长三角城市群等。我们最早出的一本书叫《江南的两张面孔》,主要讲的是江南的历史和现在。本书开篇我想谈的是“江南的三个问题”,具体是江南的历史、文化和城市。这三者很难截然分开,历史积淀在文化里,文化蔓延于历史中,同时又交集、汇聚于城市并通过这个“容器”的压缩和聚变而生发出种种“新声”和“新态”,深刻影响和有力推动了上海、江南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一 历史的“变”与“不变”: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历史属于时间范畴。正如康德说没有和空间相分离的时间,江南的历史也是和江南的空间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对江南要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江南”。但这个问题也很难明确,因为江南的版图在历史上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到底哪个时代、谁的江南才是要研究的对象?对此各有各的说辞和论证。我们借用了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理论方法,历史上尽管有很多的“江南”,但由于只有其中“最成熟的形态”才完美体现了“江南的本质”,所以也只有“这个江南”才是我们要研究的“江南”。尽管魏晋以后,由于北方与中原人口和文化的南移,江南地区在经济与文化上逐渐后来居上,但成熟形态的江南无疑是在明清两代。据此我们把李伯重提出的“八府一州”说作为江南的“核心区”,同时将“江南十府说”中的宁波和绍兴,以及尽管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联系上十分密切的扬州、徽州等也作为“江南的外延”,由此绘制出一幅以文化为边界同时又较好照顾了历史的“江南”地图。有了这样一份地图,就可以避免纠缠在“什么是江南”的争论中,把江南研究深入下去。
尽管江南最直接的存在形式是空间,但在历史长河中也必定有其源头。在江南文明起源研究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黄河中心论”,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原文明成为认识和研究江南的基本语境和判断标准。如果江南文明确系由黄河文明传播而来,自然也无可厚非。但正如李学勤说,“黄河中心论”最根本的问题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而综合20世纪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早在新石器时代,作为江南母体且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就已发育得相当成熟。由此出现了一个颠覆性的新发现,江南文明是长江文明的“亲生子”,而不是黄河文明的传播产物。在解决了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后,以往很多解释不通、解释歪了的东西,才有可能被纠正过来。
斯宾格勒有句名言:“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说,“江南的历史,就是江南城市的历史”。在任何时代,集聚着大量人口、财富和文化资本的城市,都代表着一个时代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最高成就。对于江南城市而言,一方面,各种零零碎碎、遍布江南大地的技术创造和文化智慧,正是由于最后汇集到了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上海等城市才发扬和传承下来的,另一方面,也主要是要满足江南人民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生活生产需要,江南城市才日益形成了自己的形态、功能和特色。从空间类型上看,历史学家习惯于把中国古代城市分为政治型和工商型,他们也比较一致地认为江南城市属于后者,而北方城市多属于前者。江南的工商型城市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不是政治与军事,而是经济和文化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机制。这是一条始终贯穿江南城市发展的重要线索。南宋时期的临安就已开始挣脱“政治型城市”的约束。临安尽管是南宋首都,始终面临着政治和军事的压力,但与唐代长安、洛阳、北宋汴梁不同,它的文化消费功能异常发达,有时甚至可以与政治和军事平起平坐。这也是诗人林升说“西湖歌舞几时休”的主要原因。在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就出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城市网络,有着明确的层级体系和经济分工,这和几百年以后西方的“城市群”已经很接近。当时的江南城市群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仅在经济财力上支撑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也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审美趣味、风俗时尚等方面占据了“文化领导权”,后者的影响有时还甚于前者。在从近代向现代演变过程中,江南所培育出的上海,特别是在中西文明交流和文化杂交下缔造出的海派文化,不仅一直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杰出代表,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20世纪中期以来,作为城市高级形态的城市群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江南这个美丽的名称逐渐淡出,今天人们说得最多的是长三角城市群。和历史上的江南地区一样,长三角的范围也先后经历了1996年的14城市版、1997年的15城市版、2003年的16城市版、2008年的25城市版和2016年的26城市版等变化。表面上看来,今天的长三角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江南地区的传统版图,两者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之所以有今天,离不开明清时代的苏州、杭州、南京、扬州和近现代的上海、无锡等城市几百年的积累和奋斗;另一方面,以2017年上海“2035规划”提出的“上海大都市圈”为标志,长三角的核心区仍未超出明清时代的“八府一州”的范围。这可以称之为“万变不离其宗”,也是今天研究江南和江南文化的旨归。
二 文化的“是”与“不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多年以前,在《江南话语丛书》的总序中,我曾写下这样一句话: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江南无疑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但同时也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这个农业文明时代创造的典雅、精致、意境优美、情味隽永的精神家园,在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社会的几度风雨之后,正变得越来越遥远和陌生,正所谓“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如何找回中华民族魂牵梦萦的江南?其实并没有什么方便法门,我们给出的一个答案是“先知后行”,即先要在头脑中弄清“什么是江南”,或者说“什么是江南的美”,然后才是在现实中的重建或复兴。事实上,由于不认真研究“什么是江南”,现实中的“东施效颦”已经很多。本着这个初心,我们便开始了江南文化和美学的研究。
尽管人们常说“知易行难”,但我们体验更多的却是“知难行易”。以往的江南研究,一是偏重于文献整理与研究,它们或是卷帙浩繁的集大成,或是各类专学的资料汇编,但大都局限在文字、版本校订和资料收集上,这种“故纸上的江南”很少去触及“江南文化的现代价值与美学意义”,与人们的生活关系不大。二是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尽管突破了“资料文献整理与汇编”的局限,但它们主要揭示的是“江南文化的功利价值与实用意义”,而诸如“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沾衣欲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杨柳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人生只合扬州老”“三生花草梦苏州”——这些中华民族心目中最看重的江南意境和精神差不多“集体失踪”了。尽管可以说,没有文献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研究,就不可能还原出江南的历史真面目,但在当下更要强调的却是,如果只有文献学的江南、经济学的江南和历史学的江南,那绝对不是中华民族内心深处那个能够安顿生命和灵魂的家园。
为了把在现代学术中“被遮蔽的诗性江南”找回来,我们尝试提出和建立了“江南诗性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这和我个人过去的“中国诗性文化”和“中国诗性美学”研究有关。其间的历史关系和逻辑关系既密切又复杂,这里从两方面予以简要说明。
首先,“中国诗性文化”主要是在和“西方理性文化”的比较中提出的。从文化起源的角度看,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是诗性智慧。在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诗性智慧一分为三,出现了以理性文化为核心的希腊文明、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古印度文明和以诗性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明。从历史流变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历史载体。以“情”见长的唐诗和以“理”胜出的宋词,在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和一种“诗化的理性”。有了这两样东西,中华民族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和理性文化,中华民族最重大的创造则是诗学和诗性文化,这两者也再现了中西民族在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异。科学和理性文化的最大问题是造成了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机械地对待生命和残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生产生活方式。而诗性文化最深刻的精髓在于:在肯定个体感性欲望的同时,又能较好地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程度;在征服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也能有效避免天人关系走向彻底的分裂与对立。中国诗性文化为江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语境和方法。比如以往人们在讲到明清江南的感性解放思潮时,总喜欢套用西方的自然人性论、现代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但从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出发,就可以知道,江南人的“情”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这种经过诗性文化改造的本能与西方人讲的“原欲”“本能”并不是一回事儿。
其次,“中国诗性美学”主要是在和李泽厚的“审美积淀说”的比较中提出的。“审美积淀说”的基本意思是,艺术与审美活动最初都是实用的,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只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原有的政治、伦理、宗教等现实功利逐渐失去,然后才成为无利害关系的“自由”和“愉快”。笔者一直认为,这是目前把美和美感的本质讲得最“通透”和最“通俗”的学说,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说积淀说“错”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是,它只能解释人类审美实践中的部分经验,对中国则是比较适合解释中原文化圈的审美经验。从世界范围看,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早在3万年甚至更早以前,人类就开始有了审美体验和艺术创作,根本不需要等到政治、宗教等都比较成熟的文明时代。这意味着审美能力是人的天性,而不一定是后天的经验的产物。从中国范围看,这就涉及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南北文化之辩”。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在古代中国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中原文化,在深层结构上主要呈现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实用性很强的“伦理美学”。但在长期处在政治边缘的江南地区,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表现为一种“经济—审美文化”,同时也在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孕育了相对纯粹的“诗性美学”。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判断标准,也是不应该混淆在一起的。比如江南地区自古就盛产优美、多情的爱情诗,但在古代诗歌评论和士大夫的文章中,它们却常被冠以“有伤风化”“有失风雅”“淫佚”等恶名,这主要是因为戴上了伦理文化和伦理美学的“有色眼镜”。如果从“诗性美学”的角度看,它们都是基于恩格斯所讲的“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1]是两性之间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和最正常、健康的感性生命活动。
西方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未免有些夸张。但如果我们说至少有三种江南文化应该是完全成立的。一是“江南物质文化”,如所谓的“鱼米之乡”“苏湖熟,天下足”等,它们奠定了江南的经济基础。二是“江南社会文化”,如所谓的“晴耕雨读”的乡村、“西湖歌舞”的城市、工于算计和遵守规则的众生相等,它们构成了江南的社会环境。三是“江南人文文化”,这是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的江南,也是中华民族倾心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家园。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最能代表江南?笔者一直认为,尽管江南以富甲天下著称,但古代的天府之国在物质文化上并不输于江南,故物质的江南并无根本的独特性。江南自古也崇文好礼,但在这方面孕育了儒家学派的齐鲁地区也许更有代表性。在这个意义上,真正使江南成为江南的,不是财富,也不是礼教,而是由于江南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中原实用文化、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审美自由精神是古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所以说,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最高本质。
“失去了才知道珍贵”,这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经验教训,也适用于江南文化。例如在空间和建筑方面,古代江南园林集中体现了诗性文化的审美理念与要求,融入大自然和融入社会成为主要的空间功能和特征。但在今天的江南城乡,由于西方理性建筑文化在理论、技术和方法上沧海横流,各种“洋大怪”的地标建筑已把传统的江南机理和文脉改造得面目皆非。这是“西方理性文化”驱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结果。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也是如此。在李渔等江南文人的笔记中,经常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叙事,就是江南人的精致、讲究与北方人的粗放、毛糙的对比叙事。如《长安客语》中有一首歌,写得既夸张又形象:“门前一阵骡车过,灰扬。那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绵袄绵裙绵裤子,膀胀。那里有佳人夜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那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2]但受社会的“麦当劳化”和网络粗口“漫天飞”的影响,历史上“铁马秋风塞北”和“杏花春雨江南”、“关西大汉”和“吴侬软语”的区别,也早已成为追忆之梦。
当然,一种文化的沧桑巨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各方面,不会只是由于一个原因。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不是今天的江南地区不富裕,也不是因为这里的文教事业落后,但为什么今天的江南变得越来越不像江南,我们只能说这是因为失去了“江南诗性文化”的灵魂。如果认可这种典雅、精致的古典文明生活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乡愁之一,它的传承和重建与新时代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高度一致,那么从美学、文化角度研究和阐释江南文化,就不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拥有了独特、隽永、厚重、深长甚至有些紧迫的时代意味。
三 城市的“返本”与“开新”: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城市化国家。人们一切的努力与奋斗,最终都要落脚在城市中“过上美好生活”。而在中国文化谱系中最具诗意和诗性的江南,自然也是“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最重要的生态和人文资源。
但在当下江南文化的研究和重建中,却有一种很不好的思潮和做法,它们希望通过远离城市和在与城市化“对着干”中去守护和传承。这些思潮和做法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不了解今天的城市化是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想以“在山泉水清”的方式“遗世而独立”,不仅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也只能把生动活泼的江南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二是不了解江南诗性文化和江南城市在历史上的内在密切关系,也忽略了今天的长三角对江南诗性文化特有的深层和强烈的需要。尽管出现这些思潮和实践有现实原因,由于经济开放发展尺度较大以及与世界发达城市联系比较密切,各种“贪大、媚洋、求怪”现象在长三角比在其他地区更加突出。但这种拒绝现实的方式过于消极,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江南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异化问题,本质上是因为只有一个西方参照系的结果。对西方城市发展观念、规划理论、设计技术等的机械模仿和盲目崇拜,是导致长三角城市规模失控、功能紊乱和越来越不适合人们生活的根源。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城乡空间的“去中国化”和“去江南化”,最重要的是要找回另一个参照系,这就是历史上的江南城市。
从形态上看,在作为江南成熟形态的明清时代,当时的城市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成熟程度。据城市史家的统计,在明代全国50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江南就有应天(南京)、镇江、苏州、松江(上海)、常州、扬州、仪征、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10余个。在世界范围看,在18世纪共有10个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其中中国就占了6个,分别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和广州,江南地区占据了4席。也有研究认为,到了清朝中叶,苏州已发展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的特大城市。江南地区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城市,为这个地区城市化的进一步升级奠定了雄厚基础。所以我们提出,借助环太湖地域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模式,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已不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城市,而是最终形成了我们命名的“江南城市群”。而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这里。
从功能上看,江南城市群可以说已很接近理想的城市群。正如芒福德认为希腊城市比罗马城市、比今天的西方大都市都更好地实现了城市的本质一样,这不是因为经济发达和交通便捷,而是因为提供着“生活价值和意义”的城市文化。文化的核心作用在于提供一种良好的价值纽带,使原本在经济利益上激烈冲突的城市结成命运共同体。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一直十分曲折,至今在资源、产业等方面的冲突与无序竞争仍比较严重。其主要原因是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只想“支配”和“虹吸”而不想“服务”和“外溢”。但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群,天然地形成了中心城市“支配”功能与“服务”职责的和谐,这非常有利于江南城市群的功能互补和共存共荣,所以在明清时代都发展得非常好。还可以补充一句,如果说,今天的长三角之所以在中国城市群中表现优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清时代江南城市数百年的“家底”,那么也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推进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之所以历经曲折和反复,与维系区域经济社会的江南文化机制老化和新的文化联系机制一直未能建立起来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长三角城市群一直是中国城市的骄傲。但与西方相比,最大的差异不是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甚至也不是高科技,而主要是城市文化和现代服务功能。在新时代推进长三角城市群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研究和建构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已经学习得太多、需要加以规范和治理的西方理论和模式,另一个则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冷落和被忽视的江南文化和江南城市群。以后者为根基和资源,在已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增加上海“文化大都市”和“长三角世界级文化城市群”的战略定位,既是江南文化在新时代的新使命,也是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应有的战略考量。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9-90页。
[2]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