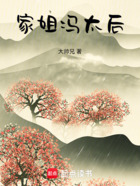
第33章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
自太和三年正月始,冯珙在大司农少卿的职位上已经待了整整六个月。
这半年里,冯珙办事认真,对人恭敬,即便是对办事的下属,也态度和善。
深受同僚们的好评。
至少表现上都是各种赞许。
也是这半年,冯珙眼看着这大魏的形势突然急转直下。
拓跋濬志在整顿吏治,多次下令查处官员贪腐,严查各地仓储情况,始终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反而在严厉查处后,各地仓储问题一下子层出不穷,今日仓储被火烧了,明日仓储被水淹了。
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拓跋家当国也深知这一道理,将设置仓廪、储备粮食作为治国的头等要务之一,如今这情况,眼看着就要出大事了。
拓跋濬的整顿,不但没有遏制住贪腐,反而加剧了腐化的鲜卑贵族对地方百姓的压榨。
好,你皇帝要查这仓廪,我伸不进去手,我认了。
但是我的损失谁来承担?
皇帝我惹不起,这些贱民我还惹不起吗?
然后这些鲜卑贵族便大量侵占百姓土地,大肆进行土地兼并。就连那些负责查处贪官污吏的官员、使者,也有不少被他们拉下了水,跟他们沆瀣一气。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数以十万计的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了所谓的“流民”。
鲜卑贵族们将这些“流民”隐匿起来,让他们为奴为婢。
加上朝堂征发大量劳役,征调各地物资和工匠,为修建平城灵岩寺(云岗石窟)做准备,百姓已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拓跋濬多次下到民间,体察民情,深感百姓困苦。
当然也就只是深感百姓困苦,工程不停,地方的贪腐和压榨也没有停。
拓跋濬登基初期实行的轻薄徭役、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他登基第六个年头里,已经名存实亡。
……
平城,李宅。
“哼。”李铉冷笑一声,将手中的信扔进了炭炉,火苗腾起,将纸上的字一口吞噬。
“不自量力。”李铉幽幽地说道,“这仓廪要是真的查下来,得砸了多少贵人的饭碗,死多少人啊……”
“尚书说得是!”他的亲信开口附和,眼神中充满了愤慨,“自我大魏立国以来,就已经如此,尚书勉力维持仓廪的收支,已经不易,这冯珙当真是不知好歹!”
“谁说不是呢?”李铉点了点头,“当初他来的时候,见他知礼节,还以为他是个懂规矩的,谁知道居然是条不讲理的疯狗。”
“他自以为给小皇帝办事,就能升官发财?”李铉不屑道,“做梦去吧,从古至今,给皇帝当刀子的,又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他真以为有个当皇后的姐姐就高枕无忧了?拓跋家的皇帝,可是有一个赛一个的无情,也不看看当年拓跋寿乐和长孙渴侯的下场。”
“那冯珙不过是个得势小人,哪里能像尚书这般看得清形势呢?”
“若是这冯珙和你一样听话就好了啊……”
“小人素来听尚书的话……”这名亲信眼神柔媚似水,竟比女人还女人,直勾勾地看着李铉。
李铉微动,招呼着他,“过来。”
亲信听话的走了过去,自觉的跪在地上。
“嘶……”
……
细数整个北魏皇帝,冯珙觉得拓跋濬已经是能力很强的一位了。
他上位以后采取的各种措施,都保障了皇权的稳固和国家的安定。
百姓也过上了几年的好日子。
但是作为鲜卑贵族集团扶植上位的皇帝,他的立场天然就倚向鲜卑贵族。
崔浩当年“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提高了汉人高门的地位,还有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这都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鲜卑勋贵的跋扈,本质上是服务于拓跋家的统治。
拓跋濬登基后不久,就颁布《复佛法诏》,鲜卑人信仰的佛,再一次回到了北魏的大地上。正所谓上行下效,因为拓跋濬信佛,皇后信佛,底下的文武百官也都信佛,所以佛教甚至将儒、道两家都碾在了身下。
佛教将儒、道碾在了身下,就如同鲜卑人将汉人碾在身下。甚至连是否会说鲜卑语,都成了判断一个人是否高贵的标准。
拓跋家治国真的不太行。
拓跋濬已经算是其中佼佼者了,可还是不够。如果拓跋濬是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皇帝,或许他能将这个王朝带向鼎盛。但是北魏是一个鲜卑人建立的地方性政权,没有实现大一统,民族矛盾尖锐,拓跋濬能做到的就是承上启下,勉力维持罢了。
孝文帝也很厉害,但是更多的时候也不过是循旧例,加深度罢了,他的改革都是在冯太后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汉化。可以说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为后面的六镇之乱埋下了隐患。
真正将北魏带到鼎盛阶段的,是冯珙的姐姐冯有,也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冯太后。
现在的冯有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眼光。
在冯珙被召进宫中与冯有交谈时,冯有就曾对冯珙说过一些她的想法,其中就包括官制、土地等方面的改革。
只是冯有并没有说得太深入,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深宫妇人,能够有这样的见识,已经足够让人心惊了。
冯珙近些日子又是加班加点,仿佛回到了年前担任给事中的那段时光。
而且形势更加紧迫,也更加危险。
大司农卿名为步六孤斤,太武帝时期,任大司农丞,景穆太子拓跋晃执政时,升任大司农少卿,期间又转任地方担任刺史。
拓跋濬登基后,又任命他为大司农卿。
冯珙了解完这位大司农卿的底细后,只能说叹为观止。
从七品的大司农丞,到身为九卿的大司农卿,若是他有心阻挠,都不需要开口,底下就有一大堆人会给冯珙使绊子。
令冯珙庆幸的是,这位大司农卿并不咄咄逼人,甚至非常和善,当然,也不怎么管事。
给冯珙的感觉就是,这位上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每天端着杯茶,坐在官署里,笑呵呵地看着来回忙碌的官员。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是一句“言寡尤,行寡悔”。
当然不是在说他做事谋定而后动。
这位大司农卿的意思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兴许在他眼中,这就是能历经三朝屹立不倒,还能升任九卿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