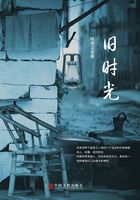
过去的中秋
唐人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言:“年年代代花相似,代代年年人不同”。意思是说每年的美景都相像,人却因岁月侵蚀而日渐沧桑。
其实,不但人随岁月而沧桑,同一年节抑或因年月变化而感受异样。
不觉间,我已度过57个中秋。倘要我谈中秋印象,仍觉茫然。儿时“过不起”中秋却老想过;如今生活好了,“过得起”了,却又觉得它单调无聊,少了昔日中秋的味道。仅成了吃“盒子比饼子贵”的月饼的由头,似乎缺了我中华年节文化底蕴的深厚。
那过去的中秋,不说传统的民族风情,单就中秋食品就很值得品评。
我能记得的最早过中秋,大概在我十岁左右。那时,父亲不幸早亡,年幼的小妹在乡下外婆家寄养,屋里空空荡荡,就剩我与四弟和老娘。而老娘在中秋节前颇繁忙,除却酱园店做工,还被抽去副食店打月饼。对此,我与四弟倒高兴,因为可常找理由到那临时作坊去观赏。不但可见打月饼全过程,还能闻到月饼的甜香,说不定抑可捡点烤煳的月饼渣来“品尝”。
老家把月饼叫“麻饼”,估计因其沾有芝麻之故。20世纪60年代初,麻饼不算贵,五分钱一两粮票便可买一个,但需加张更稀缺的“供应券”。所以,即便是中秋,也难奢求把月饼吃个够。
母亲打麻饼的作坊在一个长满青苔的青条石砌成的高墙深巷,紧挨深巷另有一废弃古庙改造的榨油坊。走进小巷,除却阴凉,便是馥郁的菜油香。听得见蒙眼黄牛拉石磨的低沉,以及榨油木杵那震耳欲聋的撞击声。加之苍凉悠长的榨油号子和庙里没被红卫兵捣毁干净的泥塑鬼神,使这里很有些落寞和阴森。油房光线昏暗,隐约可见三两个古铜色大汉来回幽幽地走。袒胸露乳,大汗长流;腰间绑根长布带,把那铁链吊起的几百斤的粗圆木“撞杆”,奋力拉起,抛高,重重撞向粘满油腻的厚木箱上的大木楔,发出沉闷的钝响。浓郁的菜油便从木箱缝隙渗出,流进石碾下面的巨型木桶。然后,圆木再被拉起,撞击,钝响。山摇地动,令人惊恐。
母亲打工的麻饼作坊的清油即是这座废庙油坊提供的,可她们“公私合营”作坊虽紧靠废庙斜边上,却比榨油坊要敞亮。
十来位妇女皆白衣白帽白围腰,围坐于宽长木板前。有的和面,有的包红糖心,有的将面团用月饼钢箍挤压成型,倒也简洁卫生。炉火正旺,一位满脸麻子的麻饼师傅,麻利地将屋梁粗绳吊下的大平底锅,按压到灶台沿,铁锅虽离开炉火,仍觉热浪烤灼。师傅在锅底刷层菜油,众人将生月饼放于撒有芝麻的簸箕里筛几下,月饼便沾满芝麻。然后将其捡入铁锅盖好,再吊回到灶上烘烤。几翻几烤,甜香溢出。压开锅盖,两面金黄。那沾芝麻面,油亮放光。芝麻饱满,繁星般的闪。偶或几个烤煳的,师傅顺手扔进竹篓,待官员来估价贱卖。煳饼既属“处理”,自然较便宜;且不收供应券,相当划算。母亲有时亦买点,年幼的我们方得以“尝新鲜”。而刚烤成的麻饼,烫得要命。掰开来,红糖炒面馅,油膏似的流。嘴巴一咬,能烫出水泡。可我们绝不会吐——晓得那是用钱亦难买来的稀罕物。龇牙咧嘴,足蹈手舞,强咽下肚。那煳的麻饼倒有种独特的煳香,其滋味令我至今难忘。仍觉它倘加点橘皮、花生,便是我最爱、亦是最好吃的月饼。
昔日的月饼不会添什么防腐剂以白增成本——各家都稀缺,能有钱买且可买到已属不易。按规定,中秋麻饼,每人仅有一个供应,很快即被各家细娃们瓜分殆尽。没等“防腐”,早已进肚,顷刻化为农家肥变成了粪土。
也因这儿时印记,我现在对咸甜交杂的火腿月饼仍很不满意;始终偏爱甜香怡人、略带煳味的红糖麻饼。然而,这种价廉物美又接近平民且中秋味十足的月饼再也无处可寻。
古镇附近“农望乡”的外婆,当年生活比我家好许多。中秋这天,外婆家不做月饼却打糍粑、煮腊肉、喝桂花酒和供月神。其中,打糍粑的场景最诱人。
先把糯米用温水浸泡三两个时辰,再倒进深木蒸子架大火猛蒸。刚蒸熟的糯米热气腾腾,使草屋弥漫米香阵阵。来俩大人,合抬大木蒸,将热浪翻滚的糯米倒进茅屋檐下早已洗净且抹了熟油的碓窝(石臼)。舅妈、表哥则高举两头粗壮、中间细长的木槌棒(也可用芦苇杆,那样,会生出种别样清香),你杵一下我杵一下,高举狠砸,把石臼里的糯米上下捶打。工夫不大,糯米便成了黏稠的糍粑。舅妈洗净手,抹点熟油,迅速伸进碓窝,将糍粑整个抱出,摔进大瓦钵。表哥李世学,在石板院支起八仙桌,桌上放个老土罐,摆个大土碗,碗里盛满石磨磨成、拌有白糖的炒黄豆面。外婆亦洗净手,把瓦钵的糍粑揪成小团摔进土罐。糍粑太烫,每揪几个,手便得在凉水碗蘸蘸。舅妈忙将土罐的小团滚满豆面,一一摔进花瓷小碗,表嫂则将小碗上面加勺白糖,喊大家往院坝中间的桌上端。
我们早已馋涎欲滴,却不能够吃——得先拜祭月神。桌中央爇烛香,中间摆上糍粑、西瓜、腊肉和石榴,倒一缶桂花酒。外婆、舅妈等大人,皆双手合十,蠕动嘴唇,态度甚虔诚。
这时,“明月别枝惊鹊”,茅院竹树环合,桂影斑驳,秋虫唱和。月色如雾似水,乡村轻烟迷离,浑然一幅水墨写意。清凉的月光把祭品及围观孩童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宛如水印木刻。祭拜匆匆而过,外婆吩咐舅妈将糍粑端点给左邻右舍。人家也回端,相互品尝。味道大同小异,却别有种乡间温馨的邻里关系。
糍粑吃完,与一帮村娃,下农田、蹚渠沟,捉螃蟹、夹黄鳝,最是中秋夜晚的有趣事。
挽上裤腿,点燃火把,轻手蹑脚到水田及沟渠下。螃蟹一般在溪流石缝间,把石头轻搬,螃蟹夜晚看不见,一动不动,其状着实憨。你伸手捏住蟹壳两边,它的鳌钳便没法施展,张牙舞爪倒好看。嬉笑一番,丢进笆笼里面。老家的螃蟹极小,虽说八月螃蟹肥,大的难觅着。常是玩一阵,即放掉。
抓黄鳝,我不行,但表哥、表弟行,我只有给他们打火把的份。他们能准确判断哪块稻田有黄鳝。下到田里,将水稻撇一边去,手指立即伸进泥,待其拔出,鳝鱼已被抓起。黄鳝不屈不挠,在指上缠绕,滑溜不得了。但入乡民之手,如何逃得掉。抓得多,做蒜焖黄鳝,味道极鲜。倘只抓了三两根,就只得摘张瓜叶包着,外面裹层黄泥,埋进灶的火灰里。待其饭熟扒出,烫得出奇。剥开黄泥,浓香四溢,轻轻一掰,肉骨分离。撒点盐及辣椒皮,那个鲜美,那个细腻,入口化渣,绝非文字所能形容的。
八月中秋,乡村细娃,爱三五成群,蹦蹦跳跳撒欢于茅屋后的小树林。或捉迷藏,或唱儿歌,煞是快乐。当年儿歌这样唱:“月亮光光,拇指烧香。烧到哪里?烧到堰塘。堰塘垮了,月亮背起堰塘跑了。”其意为何?我至今不晓得。还有一首:“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背笆笼……”。
外婆怕我们这群“欢喜麻雀打烂蛋”,过度贪玩跌入深水田,便拉长声音喊我们回茅院。我们便牵手往家走。土埂弯弯,两边是大片稻田,望之深秀而蔚然。秋高气爽,丘壑幽深,晚风轻拂,暗送桂花芬芳。真乃“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之美景,又恍若一隅偏安、不知秦汉的世外桃源。
夜晚,外婆叫舅妈将几个晒粮食的竹簸箕在茅院石坝摊开,因挨得紧密,像大月饼落在了院坝里。全院及附近的小孩团坐于簸箕,歪着脑壳,小眼瞪起,听外婆讲“嫦娥奔月”和“阳雀寻母”的故事。一边咬糍粑,一边聆听陈年旧事。泥土青草吐香,青蛙蛐蛐低唱,山梁又偶或传来喊细娃妹仔回家的声响,那喊声老长老长。起伏高低,回荡夜空里,别有一番乡村情趣。
中秋之月着实浑圆,宛如温润玉盘。竹林茅舍,天地山峦,仿佛被泼了层清泉,润泽泛蓝,有种南宋词人张孝祥的“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清澈”的恬然。儿时中秋,真让我“欲辩已忘言”。
躺簸箕抬望眼,明月皎洁,月里阴影依稀,估计那就是砍了又长、生生不息的老桂树。迷迷糊糊,我似入美梦。梦中,阳雀在清丽的叫;麻饼、糍粑山一样高;云中仙子飞下天庭,鼓瑟吹笙,邀我游广寒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