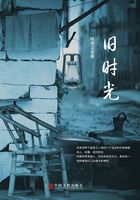
古镇端午节
儿时,即20世纪60年代初,百姓还较看重端午。家境稍好的,节前一两天,就忙着泡糯米、摘粽叶。到端午节则更闹热。
节前的晚上,全家围在油灯旁,将粽叶叠成角,有滋有味地包,心情特爽。包好就撂进铜鼎锅,用老树根焖煮到天亮。——为啥用铜鼎锅和老树根焖?——不跑气,能保温;燃得久,能使香味长留在粽子头。
端午的早饭当然是吃粽子。未开锅整个瓦屋已弥漫粽叶糯米的清香。那热腾腾的玲珑小粽,提起来一大串,翠绿油亮。剥去叶儿,红白放光。红的是蜜枣,白的是糯米。蘸点麦芽糖稀,咬一口,糯滋滋,清爽爽,满嘴粘香。
上午,各家细娃提个小粽去看划龙船,呼朋引伴,快乐得发癫。
我的老家,原本川北古镇。端午早晨,河两岸人烟阜盛,连厚实的青石城墙、百年木排楼也站满人。小镇三面环嘉陵江,东门河坝是一片松软如雪的白沙滩,几排扎有龙头彩绸、柳叶般的小木船,停靠水边。船上各立几条大汉,背心、短裤、白头巾,英气逼人。小船侧面,泊艘汽艇,打扮很是漂亮喜庆。
未几,旭日从对岸天印山吐出,山顶天光柔和清凉。古镇男人头上缠着青布巾,衔根叶子烟或抽壶水烟袋,抄手悠闲踱来,极富“甩手掌柜”的“派”。见人就打哈哈,将嘴里烟杆在衣角胡乱擦擦就递过去,非叫人家“尝一下”。然后攒成团,蹲在沙滩或鹅卵石边,“吹壳子”聊闲篇。
古镇女人则穿着蓝布大襟,领着娃儿妹仔,三五成群。你给我把沙胡豆,我给你支糯包谷,快活得很,也幸福得很,总有摆不完的“龙门阵”。
姑娘小伙这天大都穿得新崭崭,从里往外透出裹不住的青春的张扬和饱满。
我们小孩呢,光着小屁股,屁颠屁颠,沿河浅滩撩水玩。
清凉的水花偶或溅到大人身上,在端午节,不但不会遭斥责,还能讨得大人的喜悦:“这些娃儿啰,好机灵哟——”
为啥?逢年过节,大人心情多愉悦。
河坝周围,小吃颇多。有提篮小卖的,撑洋布伞的,用板板车推着的,还有就地生火现做的。叫卖声最诱人:
“炒米糖开水……”
“牛肉笼笼,嫩豆花——”
“冰糕,凉快的!”
“糖麻圆,五个钱——”。
最实惠莫过于“凉虾”。由糯米粉做成,纤细白嫩,二滩小虾样透明。于糖水碗里时隐时现,惹人眼馋。那玩意儿凉快爽极,张嘴便滑溜溜凉到肚皮,畅快且有趣。
较便宜则是绿豆稀饭下凉面,浇上四川红油豆瓣,味道“巴适得板”;脸朝河岸,或蹲或站,吃得满头大汗。
这时,河水上下游,会飘来些乌篷船,来自山外乡间,就为看古镇划龙船。河水清澈,游鱼细石,皆可目测。翠绿的山,暗红的楼,古朴的城墙,鲜活的人群,连同轻薄的晨雾,全映在蓝莹莹的嘉陵江里。层次分明,浓淡相宜,宛如流动的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挨到红日当顶,一通锣鼓声,人群立马沸腾,拼命涌到汽艇附近。张大嘴巴,伸长脖颈。细娃骑在父亲颈上,羊角辫乱晃。有的被挤下河,拉起来还咧嘴乐——那时人能容人,且豁达,很少“毛起”寻打架。
汽轮突突开到河心,放出白鸽满天飞,撒下醉鸭满河扑。
龙舟出动,如离弦之箭,锣声鼓声呐喊声,响成一片。
喊声越凶,划得越快。
江面百舸争流,白浪翻卷。
醉鸭撒满河面,东倒西歪,其态憨然,尽往水底钻。
为啥得是“醉鸭”? ——灌了酒的鸭子醉态百出才好看。
一声礼炮,几拨小伙从毛狗石鱼跃入水,随浪沉浮。惊喜声、鸭叫声、浪涛声,难以分清。有的小伙一手抓住好几只,举得老高,往木船上狠抛。那雄性的阳刚,令小媳妇大姑娘看得秋波频抛,跺脚尖叫。其激情,绝不亚于现在的“甩飞吻”,只是比“飞吻”更含蓄,更纯真。
端午这天,河边两岸的男女青年,还要对歌。歌声悠扬,曲调这样唱:
“对面的女娃瑟,哎——,来唱歌哟!歌声一响哦,表衷肠呃……”
声音诙谐明亮,常引人开怀大笑。唱热了就扑进河里去嬉戏。河水暖暖的,情歌柔柔的,笑声甜甜的,青山润润的。
这时,也有些老人妇孺坐着小船划至下河边,沿江往水里抛粽子——那是为祭祷屈原,此风俗已传了好多代,好多年。
倘碰巧,你还可见逆流而上的帆船。帆船少不了纤夫的拉纤。一条木船纤夫好些个,多弯腰伸颈,肩勒纤绳。赤身拉纤,艰难移动着帆船。
拉纤累极,挥汗如雨。必须得吼川江号子,才能使辛劳减轻些。川江号子很有蜀人的幽默与豪气。一人起领,众人相和,味道独特。领起者叫“号工”,肚里有文章,现编现唱,一天下来,不带重样。那号子有的舒缓嘹亮,更多则是苍凉悲怆,加上纤夫拼命爬行状,让你想起俄国画家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油画,感人非常。
(领):幺娃儿使力唷——
(合):咳嗨!
(领):吆涡伊紊哟——
(合):咳——嗨……
那“咳——嗨……”的声响在空谷回荡,苍凉悲怆,悠远绵长……
依古镇民俗,端午这天还得喝雄黄酒、挂艾蒿菖蒲;姑娘、小孩则需缠丝线,佩香囊。像苏轼给其忘年挚友朝云姑娘手臂缠的那样。香囊装有中草药,如朱砂、苍术、白芷和雄黄。用彩线缝上,玲珑精巧,各具形状。讲究的袋下还吊个红丝穗,蹦跳之际,馨香四溢。
艾蒿的茎叶含芳香油,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菖蒲乃多年水生草本植物,其狭长叶片亦含芳香油,能杀虫灭菌,通窍提神。端午时节将它们用红绳挂于屋檐或篾笆门,老人说它能驱邪避蛇,蛇一闻到药味就会“退避三舍”。其实,艾蒿和菖蒲极好闻,淡淡的草药味。如果用它煮水沐浴,可消暑祛毒。到端午,大人把艾蒿、菖蒲用大锅一起煮,再扯出大木盆,放于月下的天井,让我们把衣服脱尽,站在盆里狠洗。大汗一出,通泰舒服。倘用艾蒿菖蒲点燃熏烟,药香更特别,飘散得亦更远。老家人对蛇颇偏爱,那里的蛇亦温顺和善,你不惹它,它即使不慎爬到你床边,也绝不会咬你,人家只吃鼠子。
喝雄黄酒,据说能打掉五脏的内毒。端午这天,老少都得喝一点。雄黄酒淡黄微红,有些刺鼻。那种火辣辣的涩苦,铭心刻骨。烈酒给你提醒:需懂得生活的艰辛。而倘蘸它在小孩脑门上划“王”字,则不但能辟邪,什么蚊虫对你都不敢惹。
端午晚上还演戏,通常是《白蛇传》——为纪念白娘娘出钵,也叫“出雷峰塔”。当年的戏台就搭在古城楼下,大汽灯透亮通明,河对岸也看得真。惹得远地乡民,摇橹江中,坐于船舱,喝酒聊天看大戏,十分悠闲惬意。川剧锣鼓颇响亮,单听那弹戏唱腔,凄婉悠长,我至今记得许仙的唱:
“白娘子,明大义情深义厚,我许仙今遭难满面羞。当怪我迷本性自作自受……”
躺在白沙滩听戏文啃粽子,仰面是乌蓝的天,月儿也小巧,像弯弯的眉。仔细听,有涓涓的山泉,汩汩的河流与隐隐的鸟鸣。端午之夜,小雨淅沥,戏尚未完,浑身即有润湿的清凉感。空气极新鲜,吸一口,丝丝清甜。河风伴着天印山的花香草味徐徐吹来,那情那景,好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