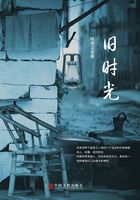
年节拾童趣
攀枝花的年节越发像个年节,未到腊月底,已很有些过年气息。昨晚与妻逛金瓯庙会便有此感觉。不必说气势恢宏的壮丽牌楼,整齐成串如长龙飞展的大红灯笼,更不必说琳琅满目的年节商品和“恐龙谷”的幽深,单那巨型充气游乐场,就很让我眼热——儿时的我何曾奢望见过和玩过?
人如蚁集,观者甚蕃。我兴奋与场内东跑西颠的小孩儿攀谈,娃娃们叽叽喳喳都说特好玩,令我很是艳羡。艳羡至极,则使我想起过去经历的年节童趣。
20世纪60年代,我国物资极度匮乏,作为孩童,自然最喜过年。无非企盼吃顿肉多的饱饭,穿件少补丁的衣衫。初一到初三,还能免去打猪草、拾狗粪、捡“二煤炭”,那卖狗粪的钱或许被娘亲批准能“抽一两角的头”,就算大人赏赐的“压岁钱”。总之,过年不干活还得钱,古镇全城任意玩,实在“安逸得板”。
自我九岁时父亲即去世,家境更为冷清贫寒,过年除却每人供应的一斤咸肉票,再无荤腥可言。娘借钱买回煮熟,分成四份,各吃各那份,少了许多纷争。而见闻近邻炊烟袅袅,肴香阵阵,在家着实憋闷,不如上街看热闹。
小镇年节在“文革”时节也没啥热闹。因禁止居民做生意,副食品皆凭票供应;除却农民渡河挑来的碧绿青菜、白嫩莲藕、鲜红胡萝卜,有限的几家公私合营店也难使小镇热闹起来。人们聚集处,多半在小店大门。乓乓乒乒,打锅盔的声音最引人,一尺来长的擀面杖边擀边敲,吆喝亦好听:
“锅盔——红糖锅盔、白糖锅盔、椒盐锅盔!”
香味已够诱人,再闻香听声音,让人馋得不行。还有甜食店的蒸泡粑、米花糖、大麻丸、炸豌豆冠等,我们细娃把街面小店围个里三层外三层。但流清口水的多,掏钱买的少。因为它不但要钱且要粮票。而粮票乃定量,谁家都紧张,多半只能“干打望”。
观赏炸“豌豆冠”,颇有趣。瘦猴师傅将泡涨的豌豆与白面加花椒和咸盐先搅拌,再舀入一个个瓷碟似的漏勺平摊。一手能提好几个,伸进翻滚的大油锅。待其在油里翻起,便倒入竹筲箕,再炸再舀,循环下去。炸好的豌豆冠酷似小向日葵,金黄油亮。咬一口,脆香滚烫,那豌豆在嘴里还爆响。惹得吃不着的细娃裂开缺牙巴羡慕笑,那真是一年少有的享受了。
我等吃豌豆冠没门。虽说那时小孩亦可赊账,但你得按时还。倘无诚信,则是最大恶行,令全镇孩童齐痛恨,父母非打得你长此记性。古训云:“人而无信不死何为?”说的就是这个理。我没偿还力,不敢做赊账生意。便伙同一帮细娃,翻进镇屠宰场晒骨头的院坝,去啃那骨头上残余的肉渣渣。
春节期间小镇杀的年猪相对多,屠宰场把骨头煮熟,撇尽油,扒去肉,将光骨头倒在院坝晒干、粉碎,以作肥料。而骨缝难免有残余肉屑,这便是我们找寻的美味佳肴。用铁钉、铅丝或竹签细撬,撬出即塞进嘴巴狠嚼。虽无盐,却极香。但你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知为何,随时有屠工来驱赶,撵得我们扑爬跟斗腿跑断。“敌进我退”,待其撤回,又赶紧返归。如此三番,像“老鼠逗猫玩”。此活儿有风险,不干又心不甘。倘“巴骨肉”撬得多,用破帽兜着,回去炒酸萝卜,就是年节上好的荤菜啰。
其实,干看杀年猪也有意思。天刚麻麻亮我们在古镇捡狗粪,老远就见养有年猪者三三两两把猪往宰杀点赶。倘有猪粪捡,我等最喜欢。乡民缠着蓝头巾,翘着叶子烟,来到宰杀点。坐在箩筐边或紧靠街屋沿,捡些枯枝败叶用火镰打燃烤火围圈圈。猪叫人吵臊气重,那年味浓得不一般。天亮,宰杀点开张。铁锅开水翻滚,满屋热气升腾,两条大汉抓住猪脚杆,摔在斜木板。屠夫上来,扳住猪嘴,一刀攮进,血“扑”地喷出,木盆接着,不会流盆外半点。褪毛、破肚,三下五除二,肉呢,肠呢,板油呢,都分类进了箩筐内。当时兴“宰一征半”,即私人杀猪政府征买半爿,否则就有“走资本主义”之嫌。形成规矩,百姓便习惯成自然。且政府只征半边肉,猪头、内脏等皆归养猪户,我家穷得家徒四壁,对杀猪过年者唯有干瞪眼。吞完清口水,再去城隍庙转转。
城隍庙着实是年节细娃们的好玩地。它坐落在北街一深巷,原本是威武硕大的关公祠堂。状若云南黒井镇的武家大院,但比武家院深远。房屋更多,早先还有旺盛香火。殿堂巍峨,高低错落;古木参天,石雕庄严。然遭遇“破四旧”,统统被摧残。大的一时铲不脱,也被凿去了石脑壳。城隍庙算作“废物利用”,改成了小镇粮库,我等再也进去不得。而庙外古树老藤,枯草犹深,曲径通幽,皆可藏身。正是玩“打仗”的好地方。一帮细娃分作两派,每人各有自制的“竹节枪”,装上小泥丸,一扣扳机,弹将出去,倘中脑门,也很生疼。春节穿得厚,当然打不痛。但其呐喊冲杀声,倒有几分战场硝烟味。
男娃子为显示阳刚,趁年节晚上练胆量:到东门城外荒坡坟场打土块仗。两队人马先各找坟墓“潜伏”,也“侦查”,还“偷袭”,最后才“总攻”。土块如雨,口号稀奇,跟电影里一样一样的。春节无月,寒星亦不多,除却飕飕阴风,便是点点磷火。“总攻”前,一片死寂黑暗。“司令官”趴在墓地正“运筹帷幄”间,突然,坟场哭声呜咽,又见磷火闪烁,紧接泥石滚动,似有鬼魂出没。群孩立起,形似鬼蜮;人鬼掺杂,汗毛倒立。只觉坟地乍裂,遇妖魔突袭。两派顷刻土崩瓦解,魂飞魄散。慌不择路,尖叫哭喊。可腿重千斤,不听使唤。有跌倒的,被踩的,掉进猪粪坑的,迎面互撞的,被树丫挂住衣衫的。一派混乱,抢地呼天,真正“惊魂于夜半”,仓皇出逃鬼门关。
年节的文明游戏,便是坐“滚珠车”、滚铁环、划甘蔗、砍瓦圆。女娃则是 “修房子”、跳绳子、踢毽子。所谓“修房子”,就是将街面青石板标上序号,摔个绣球状的布包,用单脚跳,努力把布包踢进规定的方格内便了。这需体力与平衡力,稍不留意则犯规双腿落地。砍瓦圆需先将废瓦片打磨圆,众孩童围着一斜石面往下砍,任瓦圆滚远,谁的远谁即可向滚得近的瓦圆瞄准“抛盖”。倘被盖住,那么,被盖的瓦圆主就得甘领胜者“奖赏”的弹脑门。遇到胜者恶作剧,“兰花指”在你脑门盘旋半天,就是不弹。你龇牙咧嘴,如受刑前的考验。“轰”然一声,天旋地转。众孩大笑,你疼得大叫,脑门顿时起青包。
高雅要数看胡娃阁楼放鸽子。我们小院细娃数胡娃最大,他乃家中独苗,颇显“富豪”。其家有个小楼阁,养着好些和平鸽。年节间,让参观。爬上楼层,白鸽成群,转动脖颈,可爱机灵。放飞出去,天空湛蓝,鸽影盘旋,哨音清婉,令我艳羡。
儿时古镇年节鞭炮少极,也鲜有人买得起。压岁钱多得超一元者,或许会买五分钱一版的、需用鹅卵石砸,或经木头枪撞,方可能爆响的“蚕蛋鞭炮”。经常是“蚕蛋”没爆,人先嚎叫——不是炸着手了,就是砸着手了。我家兄妹仨倒绝无此等危险,因为没钱。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尚艰难,怎会奢望有鞭炮玩?那时古镇柑橘多,我们将橘壳做成小橘灯,点亮里面的小油瓶,用竹枝挑着。到夜晚,蹦蹦跳跳去至古城楼边,听一帮古稀玩友唱川戏。那唱词极具诗意,增了儿时的我几分文化气息:
“闲步花丛,庭院传来几阵风?月朦胧,谁人月夜琴三弄?琴韵幽幽曲未终,纤纤玉手按商宫……”
现而今古楼古城早被“运动”破坏,已无踪影。但鞭炮声停,似乎仍能听见古镇城楼那板胡悠扬,高腔清亮;余音袅袅,老长老长,在细雨寒风的古镇年夜飘荡,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