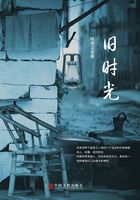
婚俗与年俗
我国古老的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俗文化显示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历史悠久、文化璀璨,胜美酒如画卷,诗意般展现出百姓和谐淳朴的中国梦。
所谓“民俗”,即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风尚和习俗,包括民族习惯和信仰等。而民俗文化,则是由民众生活、习惯、信仰、情感产生的风俗文化。对于民俗文化,正确态度应该是:既要“入乡随俗”,又要“移风易俗”。就是要充分了解、继承、发扬民俗中具民族共识、利民族凝聚、为民喜闻乐见的精华;而对其中的负面成分,则应鉴别摒弃,使民俗更民族、更优化、更具积极意义。
当前,严重问题是我们极具民族风情、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已被极度弱化。现而今,许多年轻人对民俗无知无识无兴趣,这就亟待我们去挖掘、宣传和推广,以求发扬光大;以增民族共识、民族自信、民族共鸣。
要明白,一个少自身特质的民族,是很难有多的民族认同感,亦极不利于民族凝聚的。而民俗就是最贴近百姓生活的一种大众文化。日常生活有民俗,传统节日有民俗,平时生活中的禁忌,也和民俗有关。
说个笑话,像我这姓,旧时去乘船,或许惹麻烦。
坐上小船,与船老板聊天。船老板客气问:“老先生,贵姓啊?”
我也客气呀:“嘿嘿,免贵,姓陈。”
船老板不高兴:“姓啥?”
我以为船老板没听清,对着人家耳朵放大声:“陈,陈——就是老陈。”
船老板立马翻脸,再不跟你答言。为啥?——我犯民俗的忌啦。船家最忌“沉”字:“哦,你上我船,这船就‘沉’?还老‘沉’,太不吉利了,下去吧。”
当然,你不姓陈,姓“樊”。——那更不行啦。“你上我船,船就得‘翻’?你要是‘老樊’,船还得‘老翻’?你赶紧下去你。”——这就是我们民俗中的语言禁忌问题。
倘遇人家举丧,你不感伤,还开口乱讲:“你老汉死啦?哪门死的?啷个就死瓜了嘛。没关系,化悲痛为力量,晚上打麻将,正好在灵堂”——这不是“作死”、找骂吗?
临近春节婚嫁多,我最近就朝贺了好几拨。程序大同小异:新郎新娘站于酒店,再冷之天新娘亦须穿婚纱露笑颜,新郎则言笑晏晏,给来客发喜糖撒喜烟。众人交款,寻座,与陌生同桌搭讪。看服务员端盘,听婚庆司仪神侃,观新人登台表演。新郎西装革履,新娘白裙飘逸;司仪还弄套燕尾服,其角色类似于西方之神甫:
“美丽女士请举手发誓,眼前这个人不论他富贵还是贫困,健康还是病魔缠身,啥子理由都不论,你就死心塌地的爱他,照顾他,忠于他,直至结束你的生命。请问:你答应不答应?”
女方或许想:本姑娘那么霉哟,就分来个“扶贫对象”嗦?但不表态又不得行,便假装害羞,上嘴唇碰下嘴唇:“人家啥都答应……”。
“那就拥抱Kiss下……”。
——这哪码对哪码?不是光天化日的事呀,少中华含蓄吧?
这不由我想起旧时之婚俗。
过去结婚,新人进洞房前先得吃汤圆。为图个吉利:“圆圆满满,甜甜蜜蜜”,生孩子方“顺顺溜溜”。汤圆还不能煮熟。婆婆将半生汤圆,端至新娘前,笑容满面:“哎,幺姑,‘生不生’呐?”媳妇倘不懂民俗中的“双关”,又不好说汤圆欠火,大嘴一咧,还巴结婆婆:“妈,不生。”——得,婆婆“生”了。生啥?生气了。娶你不“生”,我啥时才抱孙?
再就是出嫁得先“哭嫁”。依照民俗,结婚女子都得哭。按说结婚是喜事,不应该哭,丧事才哭。
——那就先说哭丧,这也属民俗。过去哭丧不像现在“一哩哇啦”瞎哭:“我的呀,我的呀,我不晓得哪门的呀。”——哭的内容听不出。早先不但自己哭,还请懂行的“师傅”来领哭。
灵堂设堂屋,长凳支棺木,棺木下点盏桐油灯,也相当昏暗模糊。领哭师傅一身青衣服,跪对棺木,手帕一抖,便开始哭。哭的内容全是逝者的好处,什么勤俭啦,持家啦,抽烟你还舍不得呀,尽捡人家“烟锅巴”,手被踩得“青痛”还不放呀等等。声调挺押韵,记录下来就是个唱本,类似贾宝玉《芙蓉女儿诔》的悼秦雯。但没那么斯文。只觉冷风阵阵,摇曳灯芯,哭声幽咽,墙影瘆人。
遇到“喜丧”(去世时70岁以上),表孝心,讲排场,晚上还“打围鼓”——就是一帮老年玩友围在一起唱川戏。胡琴唢呐在古镇街沿一溜摆开,汽灯挂在翘起的屋檐或树枝上,滋滋着响,把半条青石街照个通亮。倘是雨天,雨丝如线,根根如泪泉。街坊邻居穿着厚夹袄,或坐或站围拢来,抄着手,缩着脖,张大嘴巴毛骨悚然的傻听——堂屋停着棺木,黑衣进进出出,冷风时有时无,谁能不因此发怵?但川剧太好听,空气又清新,加之屋内的哭声,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通紧锣密鼓,帮腔顿起,高亢清丽:“今日一别,再难相见啊……”——当然难见,要好见还麻烦。唱的多与祭奠有关,像《三祭江》《宝玉哭灵》, 《卧龙吊孝》《桂英打神》,使人离愁别绪顿生。
——这民俗祭奠亡灵,增添亲情;培养孝道,凝聚家庭。
现在呢,灵堂哭丧改成灵堂打麻将,守灵、娱乐两不误——这像什么?
接着说“哭嫁”。
现在不兴这个——新娘化妆花几大张,你一把鼻涕一把泪,再抹白婚纱,全毁啦。但过去得哭。哭得越汹,说明对娘家越亲,对父母越孝顺。哭中难免夹杂骂,骂谁?骂媒婆:“都是那背时的王媒婆贪图那丁丁‘中介费’,硬把我说给隔壁狗二娃;我邓幺姑这朵鲜花瑟,就插在那狗屎堆上啦;害得妈老汉呃,孤单在家可怜呀……”。哭得很动情。哭得父母也老泪纵横,还来给女儿抹泪痕:“幺姑,去吧。好好对你公婆哈。你这一走瑟,就不属邓家人了哦。好了吧,狗娃外面等急啦。”
女娃把泪一擦:“要得。上轿。”——其实她早就想嫁了——我说的是现代女娃。过去的新娘哭得是真伤心,真有离别情。这风俗,无疑有利骨肉亲情的加深。
昔日女子出嫁前,还要先修面,民俗叫“开脸”。就是用两根细线把整个脸的茸毛缠一遍。表示这姑娘是光光生生,干干净净,从内到外都很纯真。
这事情大多由母亲来完成。母女盘坐床边,丝线在女儿粉脸上绷缠。娘亲一面缠一面谈,尽是孝敬公婆、遵守妇道、母女难舍的牵肠语。女儿频频把头点,加之丝线缠脸有种疼痛感,新娘忍不住珠泪涟涟。这叫“喜泪”,也叫“离娘泪”。常是母女都感动,半天缠不完。待出闺房看,两人都成红眼圈。
而男方来迎娶,需讲究聘礼。得有大红公鸡、陈年老酒,以及鲢鱼、猪心和猪蹄。这也有说道,除“红红火火连年有余”外,即表白“小婿我是有心有腿儿,专程来娶你乖女儿”,愿与她天长地久。
然而,迎娶道路颇艰辛,女方乡邻在路口故意横放几根长板凳,阻挡抬花轿吹唢呐的男方人。新郎忙下马,递烟撒糖说好话。嘻嘻哈哈闹腾好一阵,才放新郎进屋接新人。
出嫁还要唱嫁歌,我也遇见过。
一亲戚嫁女,杀猪宰鸡,在院坝摆流水席,请亲戚与邻居,旧称 “吃嫁女酒”。乡邻主动来打理。院角垒灶安锅,淘米洗菜烧火。井井有条,十分热闹。花轿一到即放鞭炮,吓得鸡飞狗跳猪拱槽。女婿乃邻村小会计,抬来几箱大聘礼,无非是上面所说的,俗称“过礼”。这在过去,已相当不易。当家老汉非常满意,捋捋胡须,感谢几句,立马开席。红苕干饭随便舀,青菜萝卜任你添,村民吃得人喜甚欢。
喜酒吃完已到傍晚。在新房窗前的竹林边,一帮姑娘媳妇,吃着红蛋,背靠青山,仰望月亮唱嫁歌:
四季豆来开白花,背时媒人夸婆家。
一夸婆家家业大,二夸婆家生男娃……
倘若在男方,便是闹洞房。然能否看见新娘,得看你的属相。——那玩意儿“学问太高深”,三两句说不清。简言就是你的属相倘跟新人“有冲撞”,就只能爬院墙、伸脖颈“干打望”。而闹洞房则是越闹越兴旺,越闹越预示新郎新娘子孙满堂。节目之一是在婚床上撒干果。常是红枣、花生和板栗。亦难免细娃调皮,摔个仙人球搞恶作剧。推搡新人躺上去,硌不硌人不管你。就为讨吉利:“早立子,花着生”。——这显然不科学。可民俗表民心:图喜庆,盼昌盛。
再往下,生娃你得取名吧,那更得讲究民俗啦。
为给婴儿取好名,父母不必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么说吧,凡是能动员的“有生力量”全上。查《字典》,翻《黄历》,抽签算命,就为取好名儿。为甚?民俗有讲啊:“好名好运”呀。
过去给孩子取小名,爱取什么:“杨兔儿,矮冬瓜;狗妹仔,猪二娃”。——这同样有民俗:贱名好养。
咱们国人办事喜欢“挑日子”,且爱挑双日子。觉得“日子挑准,办事则顺”。——这同样含有民俗中的禁忌和希望好事成双的心理。
可为什么过年过节大都在单日呢?
如:大年初一,五月端午,七月半鬼节,八月十五中秋,九九重阳——谁能知端详?
那是因为“年节”在古人眼里,大多为“不大吉利”之日子,各有所禁忌。
清明:祭奠亡人,能高兴?
端午:纪念屈原,抛粽子划龙船,早先也是忧伤日。
七月半,阎王开地狱门,放鬼魂“回家探亲”,各家忙着烧纸祭奠亡灵。想起离世的祖先,谁会开心颜?
七巧期,牛郎织女相团聚,可天亮前就得分开,是不是很伤感?
那遇到年节咋办?——咱们祖先聪明啊。每到年节,尽量搞得闹闹热热,心情不就好了吗?这天不就容易过了吗?逐渐演变,年节都成了快乐日子。现在,还有谁不想过年节的吗?可最初,年节实在不是欢乐日,是想通过欢乐让它早点过去。
譬如,“过年守岁”的民俗,据史载,西晋就有,至唐则全国流行。唐太宗亦盏灯守岁,并御笔题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因为除夕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所以,唐人孟浩然心生感叹:“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而“岁”又通“祟”,那个“年”与“祟”,按老话,当属“不祥之鬼”, “守岁”就是防守“祟鬼”的出没。过年人们爱挂桃木、穿红衣、贴红字、放鞭炮,就为对它“驱而赶之”。陆游有诗云:“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这当是宋人守岁的明证。
我在《走人户》也曾写到老家守岁的情景。现在大年三十看春晚,要闹过十二点,应是“守岁”民俗在今天的顺延。
其实,过年前即“腊八”后的杀年猪也是年节民俗文化之一,它把过年的气氛渲染得很是浓烈。
当年我家穷,别说杀猪,杀兔也没得。但过年可到我外婆家,看她家杀年猪。
天不亮就同舅妈一家将猪往乡宰杀点赶,老远就依稀望见早有长溜排队的猪和乡亲。老乡缠着厚实的长头巾,翘着叶子烟杆,坐在扁担和箩筐上或靠于街沿,张大厚嘴互相摆龙门阵。也有捡些枯枝败叶用火镰打燃烤火抱团的。柴草“噼噼啪啪”响,好像是点着的炮仗。猪叫人吵臊气重,颇有乡村年节独特的味道。
天亮,宰杀点开张。两条大汉提起猪前后腿,摔在斜木案板上,再用草绳捆紧猪脚。屠夫上来,扳住猪嘴,一刀攮进,血“扑”地喷出,圆木盆接着,绝不流盆外一滴。褪毛、破肚三下五除二,肉呢,肠呢,板油呢,都分类进到了箩筐。人们挑的挑肉,提的提肠,端的端血旺。最得意莫过于扛猪脑壳者。将猪脑壳扛在肩上,矫首昂视,得意洋洋。猪头越大越显示起家的兴旺,惹得过路者皆投来艳羡的目光。
杀年猪是喜事,得请客热闹,乡里人称做“吃刨汤”
农村就兴这样,今天你杀猪吃你家,明日他宰鹅吃他家,既吃出了新鲜,又吃出了交情,且互不吃亏。年节时分,乡亲凑在一起胡吃海塞,哪怕吃得“相与枕藉乎沟中”,也是种难得的愉快。
老家喝酒不用杯子,每桌一大土海碗,倒满60度的大红高粱酒,从每桌的长者开始喝,呷一口再依次传。没转一圈,海碗即干。满上再喝,酒过三圈,“主随客便”。那就“百相俱生”了:
有蹲在凳上划拳的,奋力夹菜的,吆五喝六的,脸红筋胀的,唾沫乱飞的,大声咳嗽的,劝酒硬灌的,东倒西歪的,抽烟喝茶的,咧嘴傻乐的,顽童逗狗叫的,少妇撩起夹袄喂奶的,招呼细娃的,嗑瓜子的,乱嚎叫的……加之端菜跑堂穿梭其间,好不热闹!从中午喝到日薄西山,地覆天翻;杯盘狼藉,东倒西颠;借酒撒疯,不辨秦汉。这才“家家扶得醉人归”。
——朋友们,这个民俗是不是透出一种和谐的乡亲情?
正月初一和十五,南方都要吃汤圆。该民俗的寓意就是合家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甜甜蜜蜜。推汤圆颇有趣,我在《大年元宵节》里有记忆,不多叙。
年节煮汤圆,那“技术”还真得先操练。不能煮破了。破了也不得说“破”,也不得说“爆”、说“裂”,更不能说“烂”。说什么?得说:“胀”——即预示你家财喜不断往上“涨”呀!
过年倘打破了碗,也不说“破”,说什么?——“岁岁平安”。多吉利呀。可谓化险为夷,化不吉利为吉利。
农村过年还时兴磨豆腐。不仅因它也是过年的好饮食,其中仍含有民俗的谐音意——年年“都有福”啊。
年节还有个民俗,那就是“供老人”。这风气,我已写在《走人户》里。
“供老人”让我们不忘先辈创业的艰辛,不忘自身的血脉根本,不忘与生俱来骨肉亲情。而如今团年大都是下馆子,“供老人”的习俗几乎消失殆尽。别以为这只是种形式,一些儿孙对待老人的行为更差劲,提起让人气愤,还是回到文本。
年节民俗的来源,大致有三点:
1.最早的年节民俗大都与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关(如:过年、七月半);
2.有的神话传奇又为年节民俗增添了神秘和浪漫(如:“七巧”,牛郎织女鹊桥会);
3.一些历史人物当作永恒纪念逐渐渗到节日里面(如:端午中的屈原)。
以上三点,经长期融合,凝聚于年节民俗里。足见我中华民俗文化的源远流长,丰富而多彩,深沉而凝重(如: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半鬼节),热闹而情浓(过年、重阳敬老、七巧)。这表现出我中华民族是淳朴善良的,重情重义的,极富才智的。
可以说:民俗能反映社会的道德风尚,可表达民众的心理和梦想。民俗淳朴,社会风气就积极向上;反之便成貊乡鼠攘。民俗跟实现中国梦关系紧密,优秀的民俗对凝聚民心大有裨益,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元素之一。

《太行晨雾》(当代 钟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