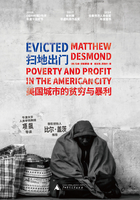
第7章 凑房租
收到谢伦娜送来的驱逐通知单后,拉马尔回到了他在第十八街跟莱特街交叉口的公寓,跟他两个儿子还有儿子的朋友打起了扑克,他们玩的是类似桥牌的黑桃王。和平常一样,他们在一张木头小餐桌前围成一圈,一会儿用力摔牌,一会儿用手腕的劲道巧妙地把牌送出去。住附近的男孩都知道,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都可以到拉马尔家吃点东西,运气好的话还能抽根大麻烟,然后很快来一局黑桃王。
黑鬼,你的黑桃打光了吧?
看好,我们要痛宰他们了。
拉马尔的对家是巴克(Buck)。十八岁的巴克是附近最年长的孩子,绰号“大哥”(Big Bro)。面对面坐着的另外两个,是拉马尔十六岁的儿子卢克(Luke)与卢克的好友德马库斯(DeMarcus)。十五岁的埃迪(Eddy)在旁边弄音响,他是拉马尔的小儿子。另外四个也是附近的男生,他们正等着上牌桌。拉马尔坐在轮椅上,把从脚延伸到胫骨上端的义肢直挺挺地搁在他的床沿,在粗木地板上投射出像人一般的剪影。
“警察都疯了。”巴克端详着手中的牌说。他是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平常会在学校的自助餐厅兼职打工。在自助餐厅工作时,他会戴上发网,包住那头浓密的玉米辫。巴克晚上睡他爸妈那儿,但白天都会待在拉马尔家。被问及原因时,他会盯着自己12码的靴子,淡淡地回上一句:“不为什么。”这群男生常一道去店里购物或者练足球,动辄九个十个人凑在一起,趾高气扬地走在莱特街上。被警察拦下简直成了家常便饭。这也是他们买大麻时一般单独行动的原因。“下一次,我就会说,‘你拦我做什么?’”巴克接着说,“我们有权利问他们嘛……他们一定是看到什么、闻到什么或听到什么有异样才有理由这么做吧。”
“他们才不用。”拉马尔回答。
“他们要啦,老爸!学校是这样教的。”
“那就是学校教错了。”
德马库斯笑了一声,接着拿打火机点了根他刚卷好的大麻烟,深吸一口后将烟传下去,牌局正式开始。一开始大家出牌很快,随着手上的牌越来越少,出牌的节奏也相应放慢。
“警察过来的时候,”巴克坚持说道,“就算你在开车时被临时检查,让你靠边停车,你的车窗也不能全开。只能开一点点。”
“想得倒美。”拉马尔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说什么呢,老爹!”巴克显然不服气。
“跟你说,不要想当出头鸟啦,”从中插进来的是德马库斯。根据拉马尔的描述,前不久他才因为“油嘴滑舌”被警察抓起来,“讲了不听,到时候苦的是自己。”
拉马尔又落井下石地补上一句:“出了事可别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我喔。”大伙儿笑得更大声了。说完他吸了一口大麻烟。“孩子啊,”他放轻了音量说,“我都五十一(岁)了,什么事我没经历过。”
“警察不会保护我们的啦。”巴克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想,但警察也不是都一个样……要是我住在一个很乱的地方,我也会希望警察好好‘清理门户’,”拉马尔丢出方块K,看了看左手边的德马库斯,“来吧,孩子,出牌吧。”方块A已经有人出过了,他估计方块Q在德马库斯手上。德马库斯看向拉马尔,厚厚的眼镜后面摆着一张扑克脸。
“老爸,邻居会罩你的……如果有人胆敢带枪来撒野,同条街的只要有枪,都会拔枪相助的。”
“小子,我打过越战啊,开枪我当然可以。”
1974年,十七岁的拉马尔看过一则广告后,跑去加入了海军。对他来说,海军生涯的记忆已经日渐模糊,无非是百无聊赖的海面,充满异国风情的风景、上岸休假的派对、吞进肚里的迷幻药丸,还有就是花钱如流水。拉马尔不懂为什么麦迪逊(Madison)那群披头散发的大学生会那么反对越战,他们被警棍打破头,甚至还在大学里炸掉了一栋楼。打仗的那些日子拉马尔很是开心,但也可能太开心了,1977年他被勒令退伍。
“子弹可不长眼,”拉马尔接着说,“听我说,先前我们不是陪德马库斯出庭吗?”拉马尔一说起故事,大家的牌就打不下去了。在开庭前,拉马尔说,他们一伙人看到有个年轻人不过才十来岁就被判刑十四年,原因是他哥哥把一个瘾君子活活打死时,他在旁边看着。“他在法院哭得撕心裂肺。”
“他们会这样乱栽赃,是因为那小毛头是黑人吧。”巴克说。
“那你还不好好想想自己该怎么做,你不也是黑人嘛。”
在巴克大笑的同时,德马库斯将牌压在桌上,是黑桃8。“这是我老妈教的!”他兴奋地大叫。黑桃王顾名思义就是黑桃最大。胜负已定,德马库斯开始收牌。
“啧!”拉马尔说。然后他把眼光移回巴克身上:“别做傻事啊,不值得……坐牢可不是开玩笑的。进到牢里你每天都得拼命,不拼你会活不下去。”
“这我知道。但有时候气到一个程度我会忍不住想出手,谁也拦不住。”
“你要成熟点啊,孩子,”看到巴克深吸了一口大麻,拉马尔马上教育他,“还有,抽这宝贝要慢一点,你这老烟枪。”拉马尔特意拖长了老烟枪三个字,声音又细又高。
被这么一逗,巴克笑得直不起身来,但拉马尔的话还是听进去了,大麻轮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客气地说:“不用了。”
当两个儿子在学校上课时,拉马尔会在家里边听老歌边打扫卫生,再来上一杯加糖的速溶咖啡。他向前滚动轮椅,拉好刹车、停住,然后将灰尘扫进带着长柄的簸箕里。拉马尔没让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单人房。卢克与埃迪一人一间,两人都有自己的床,而且还是金属床架。客厅的一角放着拉马尔的床,另外一边则摆了青苔色的沙发、与橄榄球队队友的合照、白色的假花,外加盛有孔雀鱼的小鱼缸。这是间有点空荡但不失整洁的公寓,采光充足。你可以从食物的储藏室那里推理出住户有强迫症:午餐肉罐头码得整整齐齐,各安其位;纸盒装的早餐麦片排成直线,等待检阅;高汤跟豆子罐头被分门别类,正面朝前按次序摆放。拉马尔自己改装了一个加州宝林酒庄(Clos du Bois)的红酒酒架,用来收纳餐盘,上头还放着一台小音响;福爵(Folgers)的咖啡罐里装着烟草跟午夜专属(Midnight Special)牌的卷烟纸。
这个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今天的模样。拉马尔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这里简直一塌糊涂,厨房堆积着没洗的碗盘,蛆都长出来了。但拉马尔需要个家——跟两个孩子窝在自己妈妈家的地下室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住妈妈家有“宵禁”,规定所有人都要在晚上九点前回家。再来就是拉马尔看出了这间公寓的潜力——谢伦娜免了拉马尔的押金,主要是她判断拉马尔应该申请得到“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也就是美国逐月发放的“联邦救济金”,发放对象是老年人、残障人士(肢体或是精神有障碍)等低收入人群。没想到审查结果并不如人意。
一放学,男孩子就会陆续到拉马尔家“集合”——有时是跟着卢克与埃迪一起回家,有时是不请自来。天色一暗,这群男生就会凑钱买一两根大麻烟抽,扑克牌也紧跟着开场。拉马尔的管教风格,无论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是他当自己儿子看待的其他孩子,都很开明。“凡事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所以有事也不要瞒着老爹,”他会这么跟他们说,“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好了……同样的事情我宁可你们到我家来,在我的眼皮底下做,也不要跑去街角巷尾偷偷摸摸做。”拉马尔边抽烟边与孩子们谈笑风生,顺便“传授”一些跟工作、性、毒品、警察有关的人生经验。遇到孩子抱怨女生,拉马尔会试着“秉公而论”:“你们都讲女生怎样怎样,但搞乱她们生活的好像都是男人。”拉马尔会看孩子们的成绩单,催促他们把作业做完。“他们觉得我在跟他们玩,但其实我是在看管他们。”拉马尔有办法当这些孩子的“保姆”,是因为他不会一直出门,可以值很长的班。跟拉马尔同街区的人大多都得工作;孩子们很少能见着上班的大人,除了撞见他们穿着熨烫过的制服冲着去开车的时候。
海军退伍后,拉马尔换过好几份工作。他在不少写字楼当过门房,也在阿泰亚实验室里开过铲车,负责在生产过程中倒入化学原料。不过这都是他还能走路时的事。失去双腿后,他申请过两次“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但都遭到了拒绝。拉马尔回忆他被告知的理由是对方认为他“还能工作”。就这一点而言,拉马尔不想跟对方争辩,但好工作并不是到处都有。
以前在密尔沃基好工作还真是到处都有。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老板们为了寻求廉价劳动力,不是迁厂到海外,就是把生产线搬到美国的“阳光地带”。“阳光地带”工会的力量微弱,有些甚至还不存在工会。1979年到1983年之间,密尔沃基的制造业有56000个工作机会凭空蒸发,情况比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那会儿还严重。战后那几年,此地是人人各司其职;现如今,失业率正攀升至两位数。有些幸运儿在新兴的服务业找到工作,薪水却大不如前。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观察:“1987年之前,在阿利斯·查莫斯公司的老工厂当机械工人,时薪少说有11.60美元,但在工厂旧址上重建的购物中心里当店员,你只能赚到每小时5.23美元。”[1]
这类的经济转型——当年横扫全美各大城市的经济变革——让密尔沃基的非裔劳工蒙受了重大打击,毕竟他们有半数的人都在制造业工作。一有生意要收摊,老板更倾向把旧城区的工厂关掉,而旧城区正是密尔沃基黑人的大本营。黑人的贫穷比率在1980年升至28%,1990年进一步恶化,达到42%。理查兹街(Richards Street)跟开彼托街路口曾经有一间“美国汽车公司”的工厂,位于密尔沃基以黑人为主的北部,如今这里已经变成沃尔玛超市(Walmart)。在今天的密尔沃基,梅诺米尼河谷(Menomonee River Valley)岸边那排制革厂,就像一座座陵寝,埋葬着这座城市工业时代的黄金岁月。施丽兹(Schlitz)跟帕布斯特(Pabst)酿酒厂也都关门大吉了。现在每两名适龄工作的非裔男性中,就有一名为失业所苦。[2]
1980年代的密尔沃基曾是“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进程的中心;1990年代,这儿又成了“反福利运动”的焦点。当年,在克林顿总统微调其“终结现行社会福利制度”计划的同时,一位名为杰森·透纳(Jason Turner)的保守派改革者正把密尔沃基变作一项社会福利计划的实验田。这项被命名为“威斯康星要工作”(Wisconsin Works,W-2)的福利政策打动了全美各地的立法者。上述所谓的“要工作”,可不是一句玩笑话:想领到福利救济的支票,你就得去工作。你可以去私营企业打工,也可以去做政府提供的社区服务工作,但就是不能无所事事。为推动此项福利政策,儿童保育补助和医疗补助都扩大了规模,但W-2意味着只有打卡上班的时数才能换算成福利补助,即便这份工作只是把小玩具按照不同的颜色分类;领导将它们打乱之后,第二天你便又有“工作”可做。W-2也意味着不乖乖照着这剧本走的人就会连食物券都领不到。这项福利政策让密尔沃基多达22000户家庭从福利救济人员的名册上被除名。就在密尔沃基建立了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史上第一个真正“以工代赈”计划的五个月后,克林顿总统正式签署了福利改革法案,将其列入联邦法律。[3]
就这样,在1997年,W-2正式取代“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开始提供两种不同的补助:工作者可月领673美元;未工作或无法工作者(多半因为身心障碍而不具备工作能力)可月领628美元。拉马尔被认定是未工作者,所以他领的是较少的628美元,也就是代号为“W-2 T”(W2-Transitions)的津贴。在扣掉每个月550美元的房租之后,拉马尔还剩下78美元可以过活,相当于一天只能花2.19美元。
拉马尔搬去谢伦娜的公寓没多久,上述的津贴就开始发放了。与此同时,他还收到了两张误寄的支票。而在威斯康星州儿童和家庭部(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编纂的《权利与义务指南》(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这样告知收到超额津贴的救济对象:“无论是本署或是您自己的缘故造成误发,误领的津贴都必须归还。”[4]你可以试着把这段话说给要靠福利救济支票养两名青春期男孩的单亲爸爸听。拉马尔想当然地兑现了两张支票,然后给卢克和埃迪购置了鞋子、衣服跟其他学生用品,也给新家添了些窗帘与家具。“我怎么可能不花,上面都印着我的名字了。”他对发现错误打电话来找他的社工这么说。社工将超额支付的金额从下个月的救济款支票中扣掉了,这让拉马尔积欠了一个月的房租没法缴清。
帮谢伦娜跟昆汀整理地下室,拉马尔自认应该值个250美元。毕竟地下室到处都是发霉的衣服、垃圾,还有狗粪,简直就是他的噩梦(他总是梦到自己爬进一个怪诞而阴暗的地下室买毒品)。他没让孩子帮忙清理地下室,觉得不应该委屈他们,于是独自一人将地下室收拾干净,搞到他的残肢酸痛到不行。然而,前前后后忙了一周,谢伦娜却只算他50美元,算起来拉马尔还欠谢伦娜260美元。
基本上,每个月多缴些房租来补欠款是不可能的任务。扣除固定的房租,拉马尔剩下的钱都得用来购买家用(香皂、厕纸)和付电话费。为此拉马尔按密尔沃基的行情价,以75美元卖掉面额150美元的食物券换了现金。冰箱跟食物储藏室一到月底就唱空城计。卢克跟埃迪只好跑去祖母那儿蹭饭吃,而平日来串门的孩子都知道不能乱吃拉马尔家的食物。
这么拼恐怕还是不够。若想保住这个家,就还得再找些别的差事。而从二楼搬走的帕特里斯算是给了他一件活计。帕特里斯在接到谢伦娜的驱逐通知单后并没有再争取什么,最早她就是带着三个孩子跟母亲多琳以及三个弟妹挤在一楼的两居室里。一拿到粉红色的通知单,她就默默带着孩子回到了楼下。
拉马尔盘算着谢伦娜会重新粉刷二楼,于是自告奋勇要谢伦娜将工作交给他。谢伦娜答应了,还说她会让昆汀送油漆跟工具过来。“叫他多送点,宝贝,我要组个粉刷队。”
巴克跟德马库斯都跑来帮忙了,一道的还有卢克跟埃迪,再来就是六个住附近但是把拉马尔家当成自己家的男孩儿。他们在空旷的两居室公寓里一字排开,将滚刷跟油漆刷往约19升的大油漆桶里一蘸,一层一层往墙壁上刷。他们特别认真,无声的二楼弥漫着一股严肃的气氛。过了一会,有人索性脱去帽衫和上衣,光着膀子干起活来。[5]这时拉马尔停下手,打量着眼前这幅画面。不过是去年冬天的事,他曾吸食快克可卡因吸到嗨,爬进一间荒废的房子,毒品药力退了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被困在里头,因为脚冻僵了爬不出去。从海军退伍后,回到家乡的拉马尔仍旧天天在外头饮酒作乐。1980年代中期,快克可卡因入侵了密尔沃基的街头,而拉马尔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在阿泰亚的同事会知道他不对劲,是因为刚发薪水没几天,拉马尔就连买香烟的钱都拿不出来了。他因此丢了工作,公寓也没法租了。这之后,他开始带着卢克跟埃迪辗转于收容所与废屋。晚上太冷,没被子可盖,他们就会把地毯拆开。卢克跟埃迪的母亲当时还在,但毒瘾终究让她失去了健康与理智,也让她抛弃了两个儿子。被困在废屋的那几天里,拉马尔吃的是雪。冻疮让他的双脚肿到发紫,像是烂掉的水果。到了第八天,神志不清的他从楼上的窗户纵身一跳。回首这段过往,他说是上帝将他扔了出去。在医院醒来时,他已经没了腿。此后,除去两次短暂的毒瘾复发,他没再吸过快克可卡因。
“上帝保佑。”拉马尔看着卢克跟埃迪有感而发。滚筒上的白漆像雾一样弄花了男孩们黑色的皮肤。“我有两个好儿子。”
事隔一个月,谢伦娜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车流的声响就像有人从后门丢出上千个拖地水桶般那么夸张。她这么拼,是要去参加一场会议。说得更精确点,是要去密尔沃基最南边的机场旁的贝斯特韦斯特饭店(Best Western Hotel),参加由“密尔沃基房产投资人联盟”(Milwaukee Real Estate Investors Networking Group,RING)主办的会议。出席的五十人里,有投资客、(房屋)霉菌检测师、律师,及其他与不动产有关的从业人士。不过话说回来,这群人里最多的还是房东。现场一堆男人——打着领带的小年轻们很多都是房东的宝贝儿子,在那里不停地做笔记;还有穿着皮衣,不停抖腿的中年男人;以及戴棒球帽,穿法兰绒衬衫,指关节干瘦如树瘤的老男人。[6]万丛绿中一点红的谢伦娜已经够突出了,更别说她还是个黑人。除了她三十年前从牙买加搬来的朋友罗拉(Lora)以外,谢伦娜是在场唯一的黑人,其他人几乎都是白人,开口闭口都是像艾瑞克、马克或凯西这些白人的名字。
像这样的会议,在几代人之前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那时候很多人都是兼职当房东:有些是工厂的机械工人、传道的牧师、警察,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有了房产之后(比方说通过继承),才开始觉得可以靠房地产赚点外快。[7]但这四十年来,物业管理逐渐成了一门专业,开始走上职业化道路。从1970年至今,以物业经理为职业的人数增长了三倍。[8]随着房东购置的房产越来越多,并且他们多以房东的身份自居(相对于之前提到那些偶然变成楼下公寓业主的人而言),各种职业协会与团体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配套的后勤服务、认证资格、职业培训教材,乃至于融资工具也应运而生。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51到1975年间,以管理租赁公寓为主题的出版物只有3本,但到了1976至2014年间,这个数字却暴涨至215本。[9]即便一些都市里的房东不觉得自己是“专业人士”,“住”这件事成了一门生意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天晚上的讲者是全美自助仓储经纪人公司的肯·希尔兹(Ken Shields)。在卖掉名下的保险公司后,希尔兹便开始想方设法打进房地产市场。他一开始尝试的是公寓合租,租户多是没什么钱的单身男性。“这是收现金的,钱很好赚,但我已经不玩这个了,”他一句话逗笑了全场,“做这个我有赚到钱,请别误会,我很爱赚钱,但我不爱到处跑来跑去,每天跟这些住合租屋的社会渣滓打交道。”[10]同样拥有几间合租公寓的谢伦娜连同屋中其他人一起笑了。就在此时,希尔兹发现了自助仓储这个“宝”。“自助仓储有可以跟租房比拟的利润,但……”他放低声音,眯起眼睛,“但你不用跟人瞎搅和,你只需要收他们的东西!……这简直是美国这么大个经济体里最甜蜜的部分了,保准叫你赚个盆满钵盈。”
在场的房东们都视肯·希尔兹为偶像,也不管他其实住在伊利诺伊州(而不是密尔沃基所在的威斯康星州)。当他的演讲画上句号,全场瞬时掌声如雷。
其中有个人一边拍手一边站了起来,他是密尔沃基房产投资人联盟的会长,一个留着八字胡、挺着大肚腩的男人。找不到讲者的时候,他会把会议改成“各抒己见、轮流发言”的座谈,让大家有机会集思广益。在一个举办座谈会的晚上,一名来自“铅与石棉信息中心”公司(Lead and Asbestos Information Center,Inc.)的女士一开口就对全场常因为想替房子除铅而亏钱的房东说:“铅其实可以帮你赚钱。”有名房东问到,如果检测石棉的结果是阳性,自己有没有义务向市政相关部门或租户通报。“没有,不需要。”这位女士回答。
对话继续向下推进,有其他人问到了扣押欠租人工资的事情。一名律师跳出来为全场解惑,原来房东有权申请扣押租户的银行存款,最多可以扣押其固定收入的20%,只要最后给对方留出1000美元即可。不过,领取福利补助的人不可以碰。
“那可以拦截租户的退税吗?”丢出这个问题的是谢伦娜。
律师表示惊讶:“不可以哦,有这权力的只有州长一个人。”
谢伦娜其实是明知故问,她早就做过功课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她并不是真的在问问题,而是在向现场的“艾瑞克、马克跟凯西”传递讯息,除非收到房租,否则她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不少白人房东知道房价便宜的旧城区是块赚钱的宝地,但不要说有时得送驱逐通知单给租户,光是想到要去密尔沃基的北部收租,许多人就会紧张地打退堂鼓。谢伦娜希望这些白人房东知道可以找她帮忙,只要价格合理,她会替他们管理房子,或是提供咨询意见,比如贫民窟的何处可以置产。她愿意以中介的身份做他们与密尔沃基黑人之间的桥梁。会议结束后,白人房东果然把谢伦娜团团围住。当天谢伦娜穿了件背上用水钻贴成“Million Dollar Baby$”(百万美元宝贝)字样的牛仔外套。她一边谈笑风生,一边收着名片,嘴里还不忘提醒大家:“北部没什么好怕的!”
就在其他人离席后,谢伦娜跟罗拉在走廊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讲话。“我碰到倒霉事儿了,”谢伦娜开始不吐不快,“倒霉透顶了!我跟那个拉马尔·理查兹又杠上了——就是那个没有腿的男人。他这个月没交齐房租。”
“他少给你多少?”罗拉的声音稍稍带着一些威斯康星东南部的口音,平素她是一名图书馆员,要比谢伦娜年长,那晚她身着深色宽松长裤、戴金耳环,还穿着一件红色的分层衬衫,十分优雅。她一边说话,一边将有毛皮衬里的大衣叠放在膝盖上。
“30美元,”谢伦娜耸耸肩,“但重点不是多少钱,我在意的是原则问题……他之前把我的墙刷得乱七八糟,当时算起来就已经欠我260元了。”
话说跟孩子们粉刷完之后,拉马尔打了电话让谢伦娜过来验收。谢伦娜到现场一看,发现孩子们不但没有把墙上的小坑小洼补好,还把白漆滴到墙壁咖啡色的边饰上,甚至忘了刷食物储藏室。拉马尔的说法则是昆汀没将填坑料和咖啡色油漆送来。“他没送你不会问吗?”谢伦娜回应道。她连一毛钱也不肯从拉马尔所欠的金额中扣除。
“然后啊,”谢伦娜接着说,“他也没跟我说一声,就把浴室的地板给铺了,还自己从房租里扣了30元。”原来是拉马尔在刷漆的时候发现帕特里斯的旧公寓有一盒瓷砖,于是他就拿这当材料,重铺了浴室的地板。他拿刷剩的油漆当胶水,把瓷砖一片片给贴上去了。“我跟他说,‘不要再自己乱扣房租了!’再说这家伙本来就欠我钱,他有什么资格自己减房租?”
罗拉换了条跷着的二郎腿。“这种人,就是在耍花样啊。可以叫他走了啦……他们满脑子都是要占便宜、占便宜、占便宜。”
“问题是,”谢伦娜又将话题绕回拉马尔粉刷墙壁的事情,“刷个油漆怎么可能要260元。”
“我找人刷一个房间只要30元,五个房间也才150元。”
“并不用那么多,20元就能刷一间了,顶多25元。”
“就是说啊!”
“反正在我这儿,就是他还欠我260元。哦,不对,我少算了,加房租他现在欠我290元。”
这两个老朋友笑了起来,而谢伦娜现在真的很需要笑一笑。
注释
[1]John Gurda,The Making of Milwaukee,3rd ed.(Milwaukee: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2008[1999]),421-22;同时参见416-18;Sammis White et al.,The Changing Milwaukee Industrial Structure,1979-1988(Milwaukee: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Urban Research Center,1988)。
[2]William Julius Wilson,The Truly Disadvantaged:The Inner City,the Underclass,and Public Policy,2n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1987]);Marc Levine,The Crisis Continues:Black Male Joblessness in Milwaukee(Milwaukee: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2008).
[3]Jason DeParle,American Dream:Three Women,Ten Kids,and the Nation's Drive to End Welfare(New York:Penguin,2004),16,164-68.
[4]State of Wisconsin,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A Help Guide,2014,6.
[5]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拉马尔与其社工的互动,这一段话是根据拉马尔的叙述写成的。我也没有亲眼目击粉刷的过程,现场是根据拉马尔、拉马尔的两个儿子和附近男孩儿的对话记录重建的。
[6]以房东为业是美国家族资本主义(family capitalism)的残余。可供出租的房产会代代相传,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房东也不算少见。参见DanielBell,The End of Ideology: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New York:Collier Books,1961),chapter 2。
[7]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4/5业主的房租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到3/4。参见George Sternlieb,The Tenement Landlord(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9)。
[8]同一时期整个美国的劳动力仅增长了50%。详见David Thacher,“The Ri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Screening in Rental Housing,”Law and Social Inquiry 33(2008):5-30。
[9]作者的计算基于国会图书馆HD1394号档案(非自用不动产,不动产管理)。这一想法受益于Thacher,“Ri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Screening in Rental Housing.”一文。
[10]2009年,密尔沃基旧城区的两居室租金行情是550美元,不含水电燃气。租同一区合租公寓的一个房间,房租平均在400美元,含水电燃气。公寓的单间出租利润比较高。《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