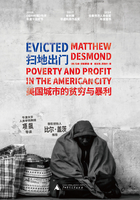
第8章 热水澡
连尼·劳森(Lenny Lawson)踏出了拖车营(trailer park)的办公室,点上一根宝马牌(Pall Mall)香烟。袅袅升起的烟雾穿过他的八字胡与淡蓝色双眼,消失在棒球帽的帽缘。他望向一排移动屋,它们挤在一条窄窄的柏油路上,几乎所有的拖车都面朝同一个方向,彼此间只有几步路的间隔。机场就在附近,每当飞机从低空掠过,露出机腹,窗户就会被震得哗哗作响,即便是已经住很久的人也会忍不住抬头张望。四十三岁的连尼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里,至于担任拖车营的经理,则是这十二年的事。
连尼知道瘾君子们大多住在拖车营的北边,那些在餐厅或养老院兼两份差(一个人轮两班)的人大多住在南边。捡破铜烂铁做回收的人住在靠近入口处。至于拖车营里“最高端的地段”位于办公室后方,里面住着喷砂除锈工人、机修工等工作最“体面”的一群人,他们的移动屋前廊都有打扫过的痕迹,而且还摆了花盆来增添绿意。靠领联邦救济金过活的人则散居在园区四周,还有那些上了年纪、一些居民口中“跟着鸡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人家也都住在园区各隅。大部分时候,连尼想把性侵犯安排跟瘾君子当邻居,但事情不可能每回都如他的意。他有次不得不把一名性侵犯安排在兼两份差事的“蜜蜂区”附近。所幸那家伙超级宅,总是待在拖车里,百叶窗紧闭,每周会有人送来食物跟生活必需品。
学院路移动房屋营(College Mobile Home Park)坐落在密尔沃基的最南端,紧邻第六街,走出去就是同名的学院路(College Avenue)。[1]园区的外围有一边是无人修剪的林木、树丛跟沙坑,另外一边则是调度卡车的发车中心。无论你想去最近的加油站或是速食店,都得步行十五分钟。学院路移动房屋营不是这一带唯一的拖车营,外头的街上尽是不起眼的褐色砖房以及倾斜得厉害的屋顶。在密尔沃基,这里是贫困白人的生活区。
梅诺米尼河谷穿城而过,就像“梅森·迪克逊分界线”一样将密尔沃基一分为二,一边是以黑人为主的北部,一边是以白人为主的南部。密尔沃基人爱开玩笑说,延伸于梅诺米尼河谷之上的“第十六街高架桥”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桥,因为“桥的一边是非洲,另一边是波兰”。1967年,曾有近两百名黑人站出来抗议这道黑白藩篱,他们聚集在高架桥的北端,朝着另一头的“波兰”走去。到桥的南端时,抗议群众尚未眼见另一阵营的面孔,就已耳闻他们发出的声音:“杀!杀!”,“我们要奴隶!”,口号的声浪甚至高过了喇叭里传出的摇滚乐。接着出现了一大群住在南岸的白人面孔,有些统计指出超过13000人。在一旁看热闹的人,开始对游行的黑人丢掷瓶子、石头,甚至对着他们撒尿或吐痰。但黑人游行队伍还是坚持往前走,按捺不住情绪的白人则开始躁动。倏忽间,一道无形的围栏轰然倒塌,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现场的白人向游行的黑人的游行队伍发起攻击,双方爆发了肢体冲突……警察也于此时发射了催泪瓦斯。
第二天晚上,游行的群众卷土重来。第三天晚上,第四天晚上……他们连续在十六街高架桥上游行了两百个夜晚。他们最先撼动了整个密尔沃基城,随后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最终连世界都听见了他们的诉求。但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1967年,《纽约时报》在社论里公开说密尔沃基是全美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挟带参众两院的绝对多数,约翰逊总统通过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与1965年的《选举法案》(Voting Rights Act),但部分国会议员因为背后有房地产相关利益团体的游说,所以不肯跟总统一起推动将居住歧视认定为非法行为的“开放住房”法案(open housing law)。后来是牺牲了一条人命(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一座旅馆的阳台上遇刺),加上后续的暴动,国会才迫于压力在同年的民权法案增修中,纳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住房政策。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公平住房法案”(Fair Housing Act)。[2]
自1930年代以来,为数不多的拉丁裔家庭开始迁入以白人工薪阶层为主的密尔沃基南部,因为制革厂需要拉丁裔男性所提供的劳动力。到了1970年代,拉丁裔的人口开始有了增长。这次白人没有跟他们干仗,而是默默迁往更南或更西边。于是“波兰”变成了“墨西哥”,密尔沃基南部成了拉丁裔专属的“城中之城”。相较之下,密尔沃基的北部仍旧以黑人为主。东部跟西部,加上连尼那间拖车营所处的最南端,成了白人的去处。即便有了开放住宅法案,种族隔离也未曾远离密尔沃基。[3]
连尼捻熄了烟蒂,钻回到办公室里。办公室位于拖车营的中央,距离仅有的出入口不远;内部逼仄,也没有窗户,纸屑东一团、西一堆,天花板上吊着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老旧的传真机、计算器和电脑都覆盖着斑斑油污。如果是夏天,空调压缩机会在底下的深红薄地毯上滴出一块巨大的水痕。到了冬天,一台运作中的小型电暖器会在塑料桶上发出嗡嗡的声响。几年前,连尼给办公室添置了不少装饰品:墙上的鹿角,帕布斯特蓝带啤酒的纪念铭牌,还有一张雉鸡展翅的海报。
“嗨。”连尼一边在办公桌前坐下,一边跟苏西打招呼。
苏西·邓恩(Susie Dunn)跟平常一样站着分拣邮件,将它们分门别类放到办公室另一面墙上的信箱里。但与其说她是把信“放进”信箱,不如说是把信“硬塞进”信箱,又快又用力。这是她的风格。说到风格,苏西抽烟时会将手紧贴住唇,把香烟整支吸进嘴里。她的习惯是说话时要同时扫地、刷东西、或重排院子里的家具,否则她会像哑巴一样说不出话来。那感觉就好像她是一只玩具陀螺,如果不想倒下,只能转个不停。苏西的先生喜欢称呼她为“拖车营的女王”,其他人则叫她“办公室苏西”(Office Susie),加上“办公室”三个字是因为拖车营里还有另外一位“海洛因苏西”(Heroin Susie),这样就不会搞混。
“失业救济金支票来了,”苏西对着一封信自言自语,“现在你是不是要交点租金啊?……你主人她要是再不缴房租,就要待不下去了。她可以搬回南部,要不然旧城区的贫民窟也可以。”
此时办公室的门开了,走进来的是赤着脚的米特斯夫人(Mrs.Mytes)。七十一岁的她是位硬朗的女性,有一头浓密的白发、满脸交错的皱纹,牙齿一颗不剩。
“嘿,奶奶。”连尼笑着说。他跟园区里的所有人都觉得米特斯夫人是个疯子。
“你猜我今天干啥了?我把一张账单扔进了垃圾桶!”米特斯夫人的脸皱成一团,她斜着眼朝连尼的方向看过去,吼叫着把这句话说完。
“是吗?”连尼看着她回答。
“我才没那么傻!”
“哦,好啊,我这边有一些账单要给你,你可以先缴我的。”
“哈!”米特斯夫人哈完这声便走出去,准备推着装杂货的小推车,开始捡破烂的一天。对米特斯夫人来说,联邦救济金才是生活的主要来源,平时捡废瓶子换到的钱则会拿去给她已经成年但有精神障碍的女儿买些零食。若是哪天“大丰收”,那她就会带女儿去“查克芝士”(Chuck E.Cheese's)开心一下,打打牙祭。
连尼笑了笑,重新处理起各种文件,只有当门再被推开时他才会抬起头。即便在别处说话没人理的人,连尼也会好好听他把话说完。虽然他的本职工作是收租跟修缮房屋、筛选房客跟发驱逐通知单,但这么做是因为他还有一项职责是“耳听八方”,他得知道拖车营里的一举一动——无论是谁忘了交房租、谁怀孕了要生孩子、谁在美沙酮里混了阿普唑仑、谁正在坐牢的男朋友刚刑满释放。“有时候我像个心理医生,”连尼会说,“但有时候我就是个大混蛋。”
拖车营的业主是托宾·沙尔尼(Tobin Charney)。他自己住在伊利诺伊州的斯科基(Skokie),距离拖车营约一百一十公里。虽然有点远,但他每天都会来园区巡查,只有周日才休息。他付给苏西的时薪是5美元,另外还给她每个月440美元的“房租优惠价”。托宾免了连尼的租金,另外还付他36000美元的年薪,统统给现金。托宾算是出了名的温柔和通情达理,但没人会觉得他好欺负。他总是板着脸孔、斜眼看人,行事风格粗鲁。他跟米特斯夫人同年,今年七十一岁,有运动的习惯,在他凯迪拉克的后备箱内,总是放着一袋健身用品。他不跟房客套近乎,更不会跟他们嘻嘻哈哈;遇到房客的小孩,他也不会停下脚步去揉揉他们的头发。托宾我行我素,丝毫不装模作样。他算是“房二代”,他爸爸以前是个超级大房东,最多的时候累积了600套房子。托宾没这么贪心,他只要有同一个地址下的这131辆拖车屋就心满意足了。
但2008年5月的最后一周,他发现连这小小的托车营都有可能保不住。密尔沃基“授权委员会”的五名委员都拒绝给他换发拖车营的营业执照。其中力主不予换照的市议员泰瑞·维特考斯基(Terry Witkowski)满头银发,面色红润,长期在南部生活。维特考斯基指出,按照市府社区服务部的记录,托宾光是近两年的违规事项就多达70次。他提到,在过去一年当中,拖车营内拨出了260通报案电话。他说托宾的拖车营无异是毒品、卖淫与暴力的大本营。他还发现由于园区内的污水管没有接好,结果秽物倒灌,十辆拖车屋的车底成了重灾区。在市府授权委员会的眼里,拖车营正在上演一场“生化危机”。
就此,密尔沃基的市议会在6月10日进行投票表决。如果授权委员会的决定获得认可,那托宾就会在一夜之间失业,而他的租户们也都将无家可归。这时候记者来了。他们头抹发胶,肩扛像武器般的相机。他们访问住户,其中有些人对托宾炮火大开。
“新闻把我们报得像没知识的杂种一样。”玛丽(Mary)在她的拖车外跟蒂娜(Tina)这么聊着。
“他们说这里是‘南部的耻辱’。”蒂娜回应玛丽。
玛丽跟蒂娜在拖车营里住了不少年,两人的面容坚韧而又饱经风霜。“我儿子为了这事都睡不着了,”玛丽说,“我跟我老公也是……你也知道,我兼两份差呢。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很拼了,但其他地方我实在是住不起。”
这时米特斯夫人走过来,她的脸眼看着就要贴到蒂娜的脸上了,蒂娜不禁后退一步。“那个王八蛋!”米特斯夫人破口大骂,“我要打电话给那个市议员,我要好好跟他聊聊!那个王……”
“你这样做没用啦。”蒂娜打断了米特斯夫人的话。
“我要去,而且我要好好教训他,”米特斯夫人答道,“那个王八蛋!”
蒂娜跟玛丽摇摇头。看着米特斯夫人气呼呼地离开,两人这才正经起来。“要叫我们搬到北部,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她说,“这玩笑开大了。”玛丽稍稍摇头,快要哭出来了,她不再直视蒂娜。
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拖车营居民最害怕的事情。拖车营里的每一个人,包括玛丽、蒂娜、米特斯夫人都一样,他们表面上在讲可能得被迫搬家,实际上担心的是住进北部。办公室苏西是园区里少数几个在北部住过的人,她已成年的儿子就曾在那里被人用枪指着。“市议员说我们这儿是个贫民窟,”她不吐不快,“我真想带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贫民窟!”这件事让苏西心中一阵绞痛,她儿子担心得将她平常吃的止痛药给藏了起来,就怕她会想不开,吞下一大把。
在议会表决前,拖车营还剩十天可以努力,居民们于是做了几件事情。他们办了场烤肉大会来招待媒体,四处打电话给地方的议员代表,另外还开始背诵要跟市议会表达的心声。像鲁弗斯(Rufus)就把想说的话写成稿子练习。平日鲁弗斯靠捡垃圾回收维生,他留着修过的红色胡须,还有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睛。“我会问,‘有谁欠过500元的房租?’有些人会举手,我再接着问,‘欠过700元的人在哪儿?欠过1000元的在哪儿?’这样子所有人都会举手。”鲁弗斯打算做出的结论是:“他(托宾)不是什么贫民窟的土霸王,也不是什么坏人。”
假如这番话不管用,拖车营最后还是得关门大吉,鲁弗斯就打算把拖车锯一锯,把剩下的铝拿去换钱。
托宾确实会给房客方便。他会让欠钱的房客今天先缴一点、改天再补缴一点。遇到有租户失业,他会让对方用工作来抵租金。有时他会跟连尼说,“这些人也许会拖欠房租,但他们都是好人。”他曾借钱给一名女租户,让她可以去参加母亲的葬礼。遇到有人喝醉了在拖车营里破坏草皮或翻垃圾被警察逮捕,托宾也会把他们保释出来。
托宾跟房客谈的条件很少写成白纸黑字,所以有时会变成双方各执一词,自说自话。房客记得她欠的是150美元,但托宾会说是250美元,甚至600美元。有一次,一名房客在申请到劳保赔偿金后,预付了一年房租,但托宾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拖车营的居民就发明了一种用语,把“托宾”当动词用(being Tobined):托宾忘记欠你的东西,就是你“被托宾”了。大部分人都会说这是因为托宾老了记性差,或者他单纯是健忘。但要说健忘的话,托宾也是选择性健忘,因为别人欠他什么,他可是记得一清二楚。
要把密尔沃基最底层的拖车营当成一门生计,需要点专业技术,也需要坚持。托宾的“策略”很简单,无论是有毒瘾的人、靠拾荒为生的人、或身体不方便的老太太,他都会直直走过去跟对方说“我来收租了”。他会捶门,敲个不停,直到对方开门为止。想要装作不在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想要隐瞒什么也非常困难。补助寄来了,你骗不过办公室苏西,因为信箱里的支票是她放的。此外,连尼也能一眼看出,你有钱买香烟或啤酒犒赏自己、或买新的脚踏车给小孩,但就是不想缴房租。房客一把门打开,托宾就会把手一伸说:“你是不是有东西要给我?”有时候他一敲门就是好几分钟,有时候他会绕着拖车拍打铝质的外墙,有时候他会找连尼或另外一名租户去后门“声东击西”,他自己则在前门“守株待兔”。他会打电话到租户上班的地方,甚至会直接找他们的主管谈话。遇到社工或牧师来电拜托说“请……”或是“能不能稍等”之类的话时,托宾就会直截了当地回应:“不然你帮他缴。”
赔了几百或几千美元的事情,托宾都会像记仇般牢牢刻在心里。他不会让欠租的人只还一半就算了,也不会用低于行情的价格把拖车便宜租出去。遇到有人拖欠租金,摆在托宾面前的有三个选项:放过对方而让自己少赚,选择将对方逐出家门,或者他可以找对方谈谈。
选项一只是摆着好看,托宾不会选。托宾是全职房东,收租对他来说是一门生意,而心太软的话他生意会做不下去。即便如此,托宾也很少真的因为有人欠租而将他们驱逐。把房客赶走意味着你得重新找人进来,而这个过程也会产生成本。通常每个月拖欠托宾租金的会有四十个人(相当于园区住户的1/3),平均每位房客欠缴340美元。[4]但托宾每个月只会驱逐当中的几个人。太强硬或太软弱都是当房东的大忌,钱要走中庸之道才赚得到。所以托宾被欠租既不会就这样认了,也不会随便赶人,他会选择第三种方法,与对方好好谈。租户一开始或许不会开心,但到最后他们都会对托宾表示感激。
杰里·沃伦(Jerry Warren)是个例外。杰里曾经是“亡命之徒”(Outlaws)飙车族的一员,浑身刺青,有好几处是在牢里文的。托宾曾经一手拿着驱逐通知单,另一手狂敲猛打杰里的水蓝色拖车(水蓝色还是他亲手漆上的)。结果通知单被杰里揉成一团丢到托宾脸上。激动的杰里吼着:“托宾,我当这通知单是屁!还有连尼,不管你多老我都照打不误!”连尼跟杰里相互喷了些垃圾话,但托宾倒没事人儿似的站在一旁。对他来说,双方这就已经开始“谈”了。果然不出几天,冷静下来的杰里自己开口了。[5]他提出由他帮托宾打扫拖车营并做一些维修的活计,以换取不被驱逐,托宾也同意了。
面对拉瑞恩·詹金斯(Larraine Jenkins),他采取的是另外一种策略。在市议会表决通过将拖车营勒令停业的一个月前,托宾曾经开着凯迪拉克载她去驱逐法庭。因为有学习障碍,拉瑞恩通过了联邦救济金的申领资格,而她之所以会有学习障碍,是因为童年时从阁楼的一扇窗户摔了下去。她每个月会领到一张面额714美元的支票,而每个月要付的租金则是550美元,不含水电燃气。拉瑞恩迟交房租已经好几次了,托宾才狠下心来带她出庭。“要把钱拿去缴房租,让人觉得很不甘心,”拉瑞恩说得坦白,“你会想说那些睡街上的人是不是比较聪明,在街上生活,没有房东也不用缴房租。”拉瑞恩坐在副驾驶座,后座则有另外一名租户帕姆·赖因克(Pam Reinke),她是位留着齐刘海、脸上长着雀斑的孕妇。托宾给了她们“明文协议”的机会。所谓“明文协议”,可以理解为民事法庭上的“认罪协商”。只要她们愿意接受、也能够严格遵守协议中的还款日程,那托宾就愿意取消驱逐。但要是她们不按协议走,托宾可以直接获得准许驱逐的裁决书,不需要再让拉瑞恩或帕姆出庭,并有权把治安官手下的驱逐队叫来(带着一份名为“财产返还”[Writ of restitution]的文件)把人赶走,大家就不必再上法庭。
在跟维特考斯基议员周旋的过程中,托宾曾经担心房客会“趁火打劫”。他怕租户会等到拖车营的命运决定后,再看要不要缴房租,但他显然是多虑了,因为大部分的租户都按时交了房租。只是这“大部分”并不包括拉瑞恩。已经欠租的她将6月的租金也先扣了下来,主要是她觉得拖车营可能会被关闭。她想如果横竖都得搬家,那还不如口袋里攒着这550美元。拉瑞恩有点得寸进尺:欠租金不说,她还跟其他几个租户上了晚间新闻,数落拖车营的种种不是。她在电视上直言看过妓女跟毒贩在拖车营里出没(让拉瑞恩去蹚这浑水的是菲莉斯·格拉德斯通[Phyllis Gladstone],支持维特考斯基议员的她是最会给托宾添麻烦的大嘴巴)。[6]在知道一切是怎么回事之后,托宾想起了拉瑞恩并没有遵守上次出庭时的“明文协议”,而这也意味着他有权请治安驱逐队将她逐出家门。既然这是他的合法权力,他也就行使了。
没隔多久,密尔沃基治安官办公室便很有效率地发了通知单给拉瑞恩,鲜黄色的纸上印着如下内容:
致现租户
密尔沃基治安官办公室
特此通知您本署现已收到法院起诉(财产返还令/协助执行令)。
您应立即自行迁离现住址;如您不能立刻搬离,本署治安官有权将您的物品强制搬离该住址。
驱逐若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您的个人财物将由本署移置至他处保管,
届时相关的损坏和损失将由身为被告的您自行承担。
搬迁人员不会将您留在冰箱或冰柜中的食物取出,
请务必自行带走食物。
看得出来,拉瑞恩被这些话吓住了。她的心情有如电影银幕般,直接投射在了脸上:高兴时她满脸放光,咧开嘴大笑,露出宽宽的牙缝;沮丧时她的脸皮下垂,仿佛有上百个铅坠在把脸皮往下拉。五十四岁的拉瑞恩独居在一辆干净的白色拖车里,但她真心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可以跟她两个成年的女儿还有外孙们团圆。这几位血亲外加上帝,占据了她宇宙的中心。她圆脸、身材臃肿,白皮肤上长着雀斑。许多年前,算是有几分姿色的她,也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男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即便是现在,拉瑞恩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她会刻意不戴眼镜出门,因为她觉得眼镜会让她看起来没那么有精神。当她想好好打扮一番、看上去美一些时,就会戴上未婚时自己购置的珠宝首饰,并且用别针把项链变长,这样就能戴得上去了。
带着一身汗味跟酸味,棕发乱成一团的拉瑞恩走进园区办公室。她把黄色的通知单像条抹布般拧得皱皱巴巴的。简短交谈之后,托宾领着拉瑞恩走出办公室,然后开始招呼苏西的名字。
“苏西?苏西!”托宾连声喊着。
“什么事啊,托宾?”
“替我带她跑一趟银行好不好?她得领点钱交房租。”
“来吧。”苏西一边招呼拉瑞恩,一边快步去开车。
当苏西带着拉瑞恩回来时,托宾在办公室里翻看资料。“领了多少?”他问的是苏西。
“我有400元。”但回答的是拉瑞恩。
“这样我不能取消驱逐哦。”托宾说,眼睛还是盯着苏西。拉瑞恩当月还差150美元的房租没交。
拉瑞恩不知所措地站着。
托宾终于正眼看向拉瑞恩:“你什么时候可以补剩下的150元?”
“今天晚上……”
托宾没让她把话讲完:“好,你就把钱交给苏西或连尼。”
拉瑞恩已经没钱了。她从准备缴纳的房租里挪了150美元去补交了欠下的燃气费,希望被切断的燃气可以恢复。她想冲个热水澡,冲去身上的味道。她想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好还能跟漂亮沾上点关系。女儿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她曾经站在桌子上给男人跳过舞,她想和当年一样清爽美丽。她希望热水可以让她的肌纤维痛好些,那种疼痛像是背上被人千刀万剐一般。医生给她开了乐瑞卡(Lyrica)跟西乐葆(Celebrex)这两种止痛药的处方,但她不是每次都有钱领药。热水或许能适当缓解这种疼痛。但事实证明150美元改变不了什么,We Energies能源公司收了钱但没有恢复燃气供应,拉瑞恩觉得自己这钱交得实在太蠢了。
苏西拿了张废纸,当成收据,把它跟拉瑞恩的驱逐通知单订在一起。“要不要找你姐姐凑点钱,周转一下,把剩下的150元交上?”她一边这么建议,一边抓起传真机上的话筒拨出一串烂熟于心的号码。“喂,你好,我这里是学院路移动房屋营,我要中止一份驱逐令,”她通话的对象是治安官的办公室,“对,案主是W-46号拖车的拉瑞恩·詹金斯。她在缴租金了。”苏西一通电话取消了治安官办公室的出勤,但只要拉瑞恩拿不出剩下的150美元,托宾还是可以重启驱逐程序。
拉瑞恩悻悻然地走回拖车。车内热到她奢望着淋浴头能喷出水来。她没有开电扇,风会吹得她头疼。她也没有开窗,只是坐在沙发上。她打电话给当地的几家社会服务机构,但几通电话都没有下文,她对着地板呆呆地说:“没有其他办法了。”拉瑞恩试着不去理会那热浪,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沉沉睡去。
注释
[1]我在之前发表的学术作品中,是以假名来称呼这个拖车营的。但在这里我使用的是真名。
[2]Patrick Jones,The Selma of the North:Civil Rights Insurgency in Milwauke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1,158,176-77,185;“Upside Down in Milwaukee,”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3,1967.
[3]关于拉丁裔族群在密尔沃基的发展历史,详见John Gurda,The Making of Milwaukee,3rd ed.(Milwaukee: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2008[1999]),260。关于种族隔离,参见John Logan and Brian Stults,The Persistence of Segregation in the Metropolis:New Findings from the 2010 Census(Washington,DC:US Census,2011);Harrison Jacobs,Andy Kiersz,and Gus Lubin,“The 25 Most Segregated Cities in America,”Business Insider,November 22,2013。
[4]这个数字是由拖车营从2008年4月到7月间的租约清册得出(连尼让我影印了一份)。这些欠款的估计数值基于夏季月份的总数得出,而这段期间正好是欠租数额和驱逐频率最高的时候,所以这里的数据会有被高估之嫌。
[5]我并没有亲眼目睹双方的言词交锋,而是跟杰里、连尼与其他拖车营的住户访谈之后重建了现场的细节。引号内的字句依据杰里的回忆如实转录。
[6]菲莉斯每个月都会准时交租,但托宾后来还是找理由要驱逐菲莉斯。连尼提议以她养狗为由发驱逐通知单给她。托宾拿出满满三页全用大写写成的褪色租约,上面规定得非常清楚:不得养狗或者其他家畜。但其实托宾和连尼都口头说过可以养,所以养宠物的居民还不少。“基本上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托宾会这么说。连尼建议托宾可以否认口头承诺的东西,然后咬住合约上的字句。租约还禁止在拖车营内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