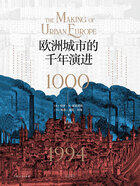
第一部分
前工业化时期:11—14世纪
稀疏散居的人类可以应付生活,但会非常吃力,缺乏很多东西……只有群居才能带来极大的便利。
—詹姆斯·博斯韦尔,
《约翰逊传》
我们对城市起源的认识依然还受着神话传说的影响。例如,据说李尔王建立了莱斯特城(Leicester),雅典娜是雅典城早期的守护者。当城市试图通过寻找或构建一种共同的传说来增强其社群感和市民自豪感时,具有神圣色彩和英雄主义气息的建城故事令城市难以厘清的过去有了轮廓。近代某些城市理论家也同样做过这种想象性推测,只是他们所提出的传说人物更加世俗化与抽象化。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制度的原型来自旧时器时代人们的坟墓和洞穴,以及由狩猎者到国王的角色变革之中(Mumford,1961);当新石器时代的村落文明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文明相融合,城市应运而生。此外,早期城镇的其他制度机构为另一些城市起源论提供了依据:甫斯特尔·德·库朗日认为城市起源于公共中心场所的建立,为着部落宗教崇拜的需要(Fustel de Coulanges,1864);另有人强调城市起源于防御工事或种种法律式的约定,后者产生了拥有各自法律和法庭的城市组织。
毋庸置疑,各种公共需求促使人们聚集于城镇。然而,人们对自卫防御和宗教仪式的希求则无需建筑永久居所也能得到满足。无论是何种政治或精神力量孕育了城市,只有大社群在经济上能够维持下去,这些城市才能继续存在。从最基本的生存层次来看,城市是人们的大型聚居地,而这些居民大部分不生产食物。因此,他们需要依赖其他地区生产者所提供的剩余粮食。同样从基本生存层次来看,除了满足生产者自我维生和下一轮耕种所需之外的产品,都可被定义为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以及将之运往城市的系统,使得城市生活成为可能。此外,假如城市能提供货物或服务作为回报,城市生活就很有机会得以持续发展,这是有可能且完全可以实现的。
古代近东地区的城市繁荣,可归功于生产技术改进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些技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方便商品和原材料的运输。很快地,拥有精密工具和船只的希腊人、罗马人在地中海盆地建起城镇,依靠贸易所得和税收供养城镇。然而,古代的欧洲城市化密集区仅限于从地中海东部城市带中心能以水路方便到达的地方。莱茵河和多瑙河成为罗马人在欧洲中部有效殖民的边界线,而英格兰和(法兰西)高卢北部的城市人口则很少。即使在罗马帝国鼎盛期,大部分城镇也只容纳了几百人,其中不少人仍在城郊的土地上务农。虽然罗马的城市化看上去面积甚广、秩序井然,但城市系统却因收集剩余产品的复杂机制与对生产的相对忽视之间造成的不平衡,而存在着极大的缺陷。无论是在乡村农庄还是城市商铺里,大部分工作由奴隶完成。除了一些土木工程上的成就,技术革新基本被忽视。如果生产力不发生重大变革的话,城市人口将难以继续扩张,甚至无法抵御外界的冲击。然而,还未等到生产力发生变革,罗马城市体系就在内部争斗和日尔曼人的侵袭下开始分崩离析了。早期的人口流失、内斗和战争逐渐破坏了剩余产品收集系统,从而大大加速了罗马的衰落。人们又退居郊野的庄园或村庄,城镇随之萎缩、消失。尽管有华丽的剧院、高架引水渠、澡堂和教堂保留了下来,但这些地方最多不过容纳一个大幅萎缩了的人口规模。正如埃迪特·恩嫩所言:“这种对人类文明有特殊贡献、独具特色的城市生活方式从此烟消云散了。”(Edith Ennen,1979:33)可见,如果缺乏为其从乡村征收剩余产品的政治体系的支持,古代城市难以存续。
随着技术和农业的更大进步,欧洲城市化迎来了又一次高潮。6—8世纪,一系列新发明促使北部农业发生变革,为从大西洋到第聂伯河地区的村落带来了繁荣。重犁、马蹄铁和马颈轭等简单工具被发明,农耕组织的革新促进了食物的集约化生产,从而带来了高产量且稳定的剩余产品(White,1972)。但城市所需的经济基础直到两百年后才最终形成,因为外来入侵者不时中断这一进程,尽管他们同时也促进了早期生产变革的传播与流通。
最终,蓬勃发展的生产力促进了人口增长,使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转向行之有效的剩余产品让渡方式,即通过贸易、掠夺和贡赋等方式实现产品的再分配,从而能够支持更多的非食品生产者再回城定居。于是,包括国王、武士、教士、商人、工匠和农奴在内的等级社会变得复杂起来。此时,社会越来越需要人们聚居到城市从事生产和分配。城市能够提供各种关系以服务于社会各阶层。住在孤立的城堡里的骑士需要盔甲、战马和马具;贵族们渴求香料和奢侈纺织品;即使是最受压迫剥削的农民也要购买外地生产的布匹、盐、器皿或各种工具;国王和神职人员的奢华需求只有远方的生产者才能满足。不断积累的社会财富和职业专业化共同孕育了贸易,并进一步刺激了产出的增长。这一贸易生产体系在聚居地内外的新开发地带蔓延开来。
所有这些听起来类似大家熟知的经济发展史,但中世纪欧洲的经济秩序并非是20世纪的微缩版。与当今市场体制、包括受国家干预的市场体制不同,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完全属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市民与所谓的自由经济人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在经济领域,主流价值观、规则与惯例旨在维护脆弱而稚嫩的生产制度,而不考虑最大限度的发展或赚取利润。工作条件、贸易条例是由地方社群、当地的世俗和宗教首领,以及行业雇主联盟共同商定。大部分地区的工匠仍通过行规掌管生产方式;付薪工作只是个别现象。在市场分散且有限的情况下,自然需要通过习俗和限制高利贷来调整贸易利润。
城市社群更崇尚对经济和个人目标的追求,而不注重传统和群体共同需求所看重的那套社会、政治和宗教准则。尽管如此,城镇仍突出地成为中世纪社会世俗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思想的汇集地。当时的城市秩序仍从属于遍及欧洲的农业等级制度。封建生产方式虽有局限性,但依然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剩余产品。城市成倍地增长,但在政治上,拥有土地的贵族对城市内外仍宣称其统治权,尽管他们越来越难以行使其权力。城市同为贵族和平民提供不可或缺的商品和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成为中世纪权力斗争中重要而独立的政治力量。尽管城市在政治、经济领域一直处于次要地位,但在意大利北部中心地区和低地国家以外,在英格兰、意大利南部、后来成为法国和德国西部的封建社会里,城市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领主建立城镇以加强对本地区的控制;国王利用城市的财富和读写文化来树立对皇室的效忠感,对抗叛乱的封臣;教会将城镇作为宗教仪式和教育的中心,教会的主教维系着城市自古以来的延续性。尽管宗教和世俗精英一直努力将具有颠覆性的城市秩序归顺其治下,但中世纪的统治形式、思想传播和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城市。即使是地处欧洲边缘的游牧社会也发展出一些具有城市功能的中心地区,而在这些有限的中心地区,城市也在争夺主导权。
大约从1000年到1300年(欧洲东部则时间更长),在长时期扩张中,中世纪城市化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将考察这一长时段城市建设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范围包括对个别城市的形成、规模和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以及对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关系偏理论的探讨。世世代代居住在城镇或为城镇进行生产的人们也值得我们关注。由于城市人口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少数群体,其人口增长的重要过程将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因素。同样,在人口统计学领域里,城镇与乡村是被区别看待的,但它们实质上又相互影响。移居城镇的乡村人口—在此生活一天、一年或一辈子—可以作为微观案例,来考察早期城市化产生的尚无定论的历史问题。
我们的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欧洲广袤大陆上发展起来的城市聚居点,将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些城市及其居民。首先,从一个基本静态的角度分析城市的物理规划、社会组织形式,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作用。而后,通过对城市发展的动态描述来揭示早期城市制度的运作情况。城市不能自给自足,因此必须配合研究确保其生存和扩张的各种相关因素。由此,我们将调查是何种因素促使一些地区进化为城市,而另一些相似的地区却依然保持原样、缺乏影响力。我们的目的在于探究城市化这一持续至今的动态过程之发轫。至于将人口(包括移民)问题留至最后讨论,这主要是为了强调欧洲的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增长的结果,更不用说是为了减轻因土地供应紧张而造成的人口压力。人口与城市规模的同步增长取决于一个复杂的进程,对这一进程的阐述可以先从经济剩余的概念着手。